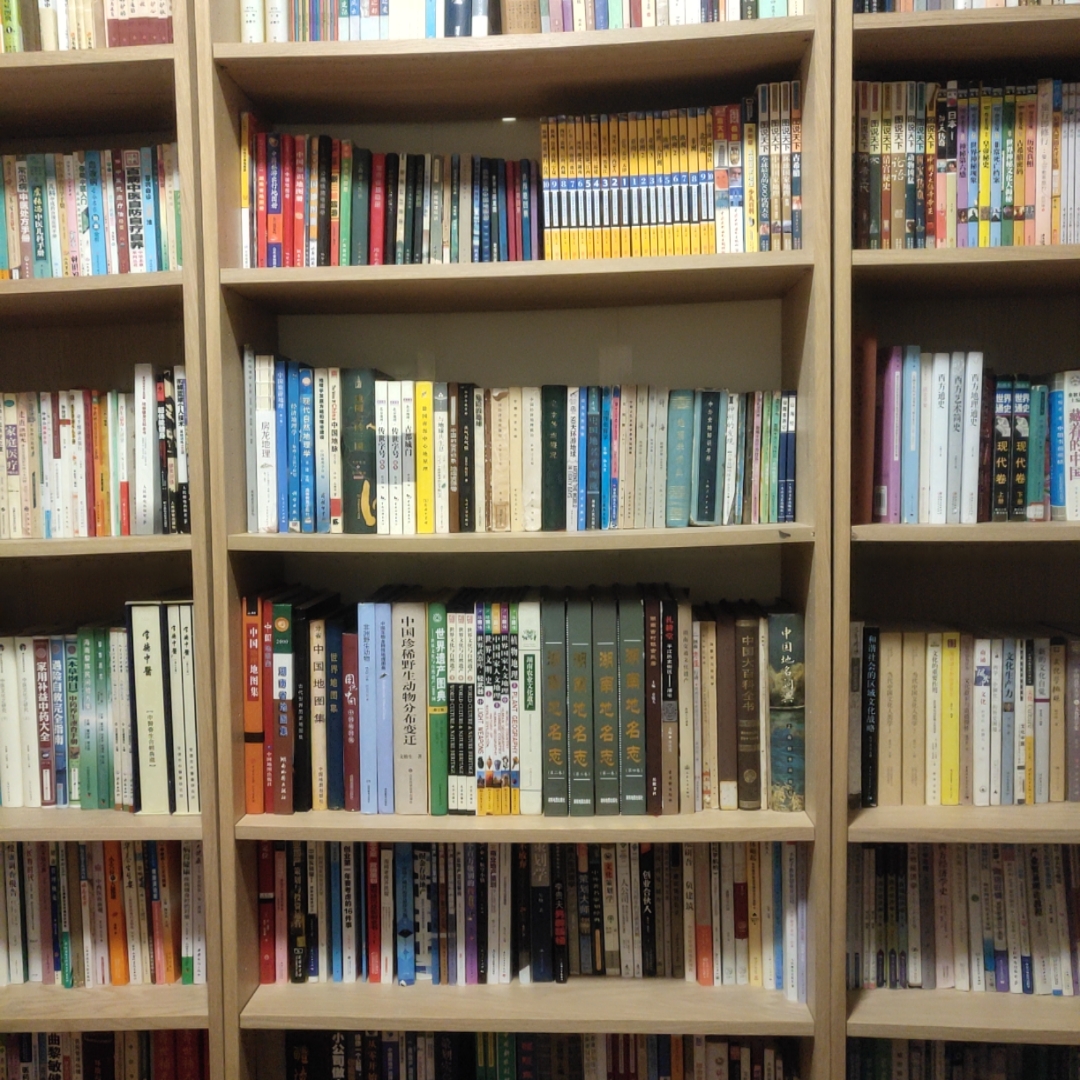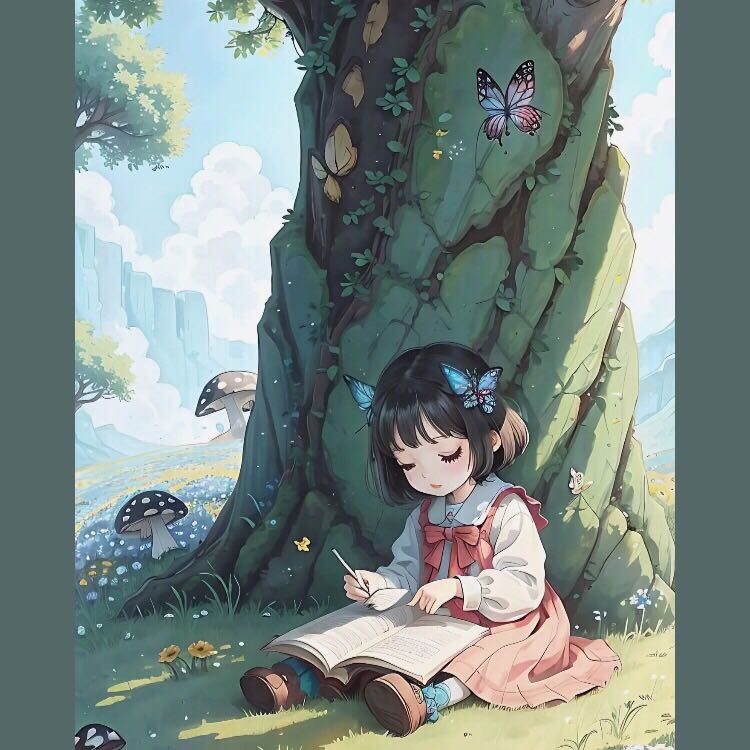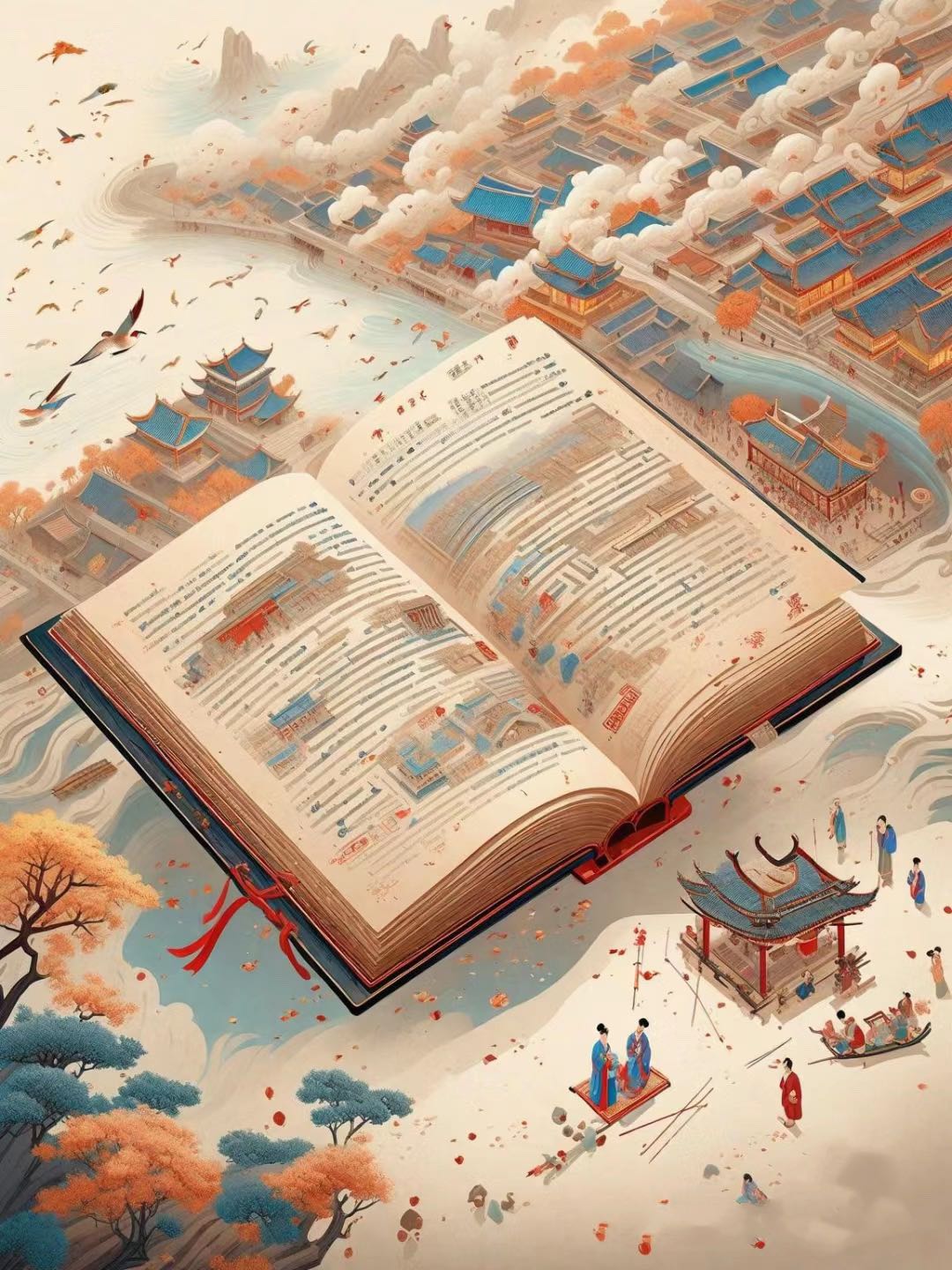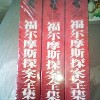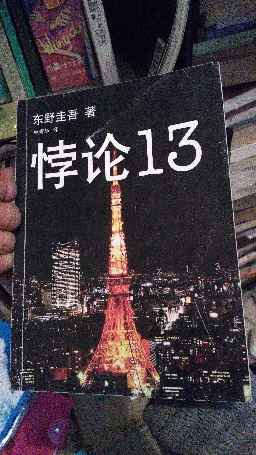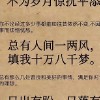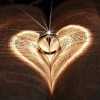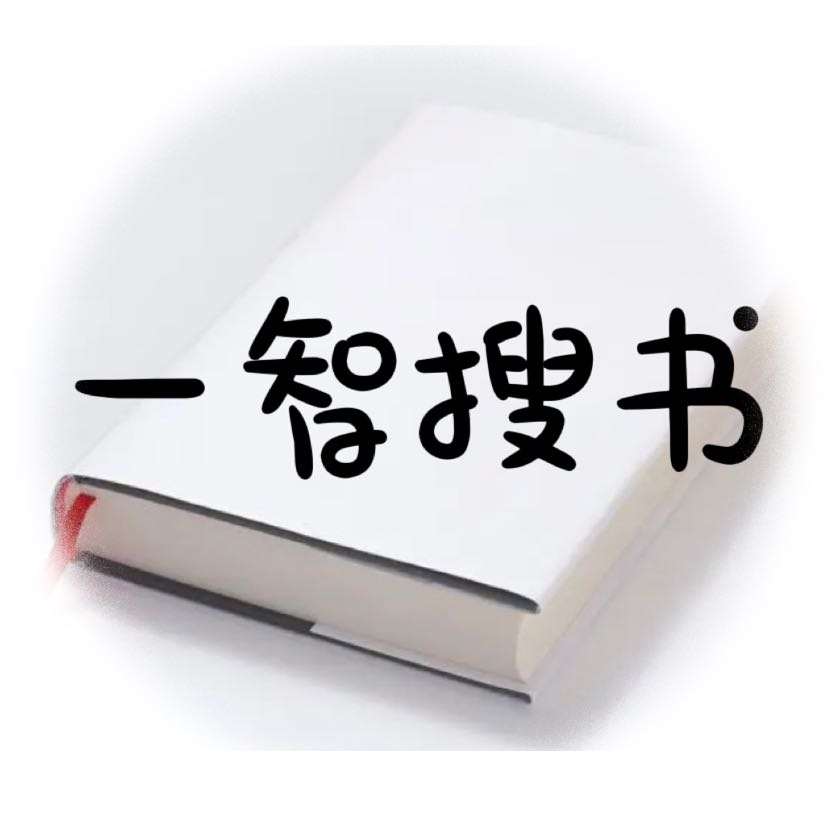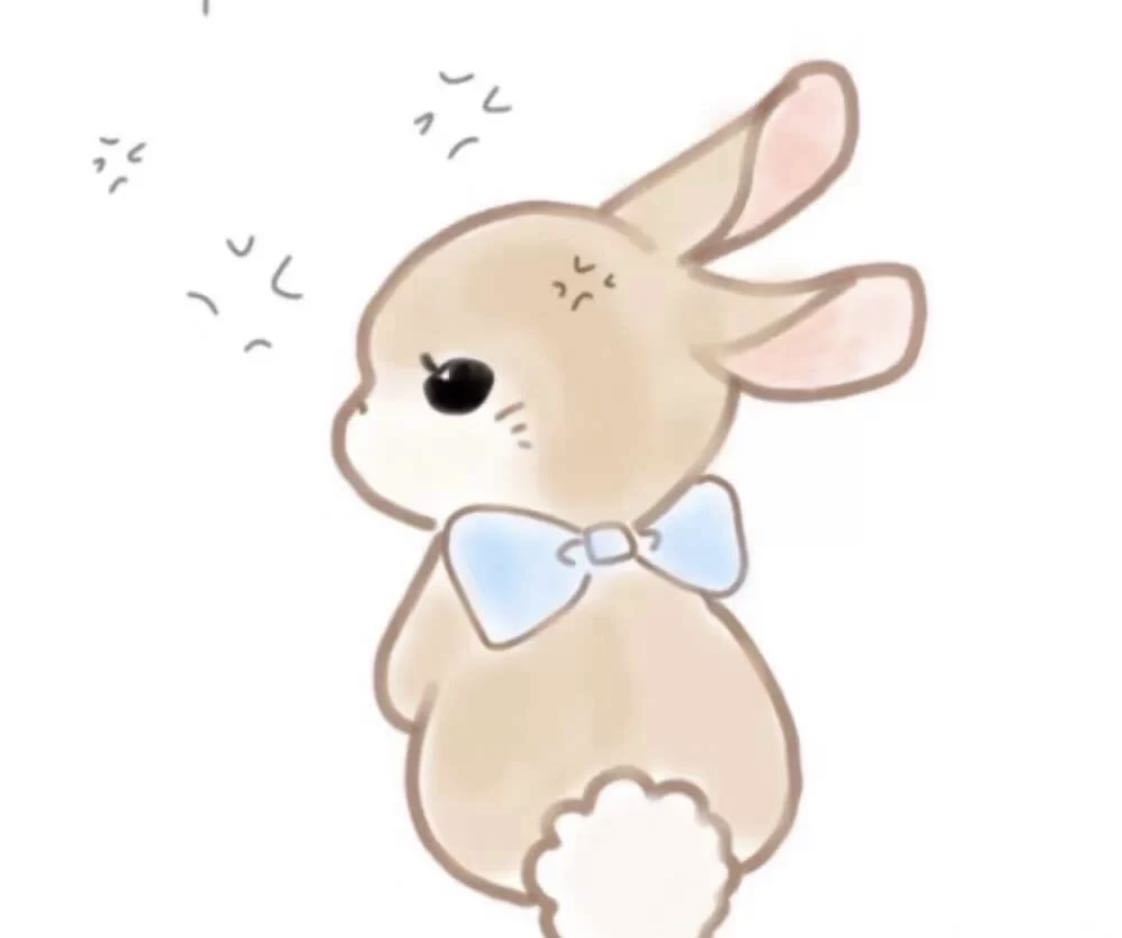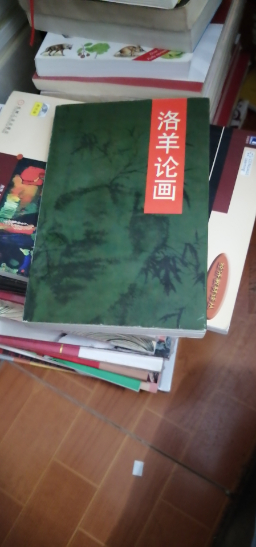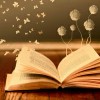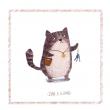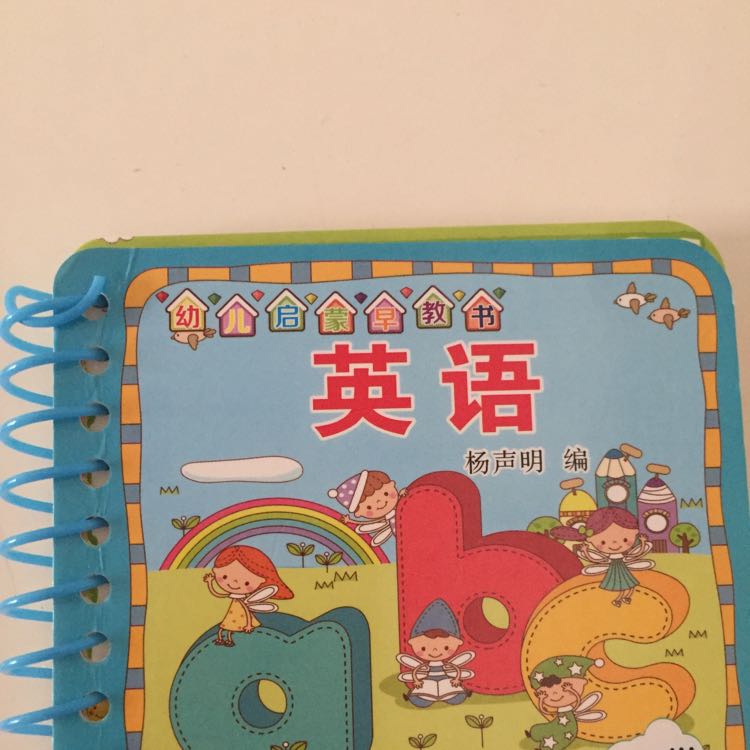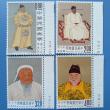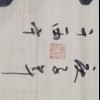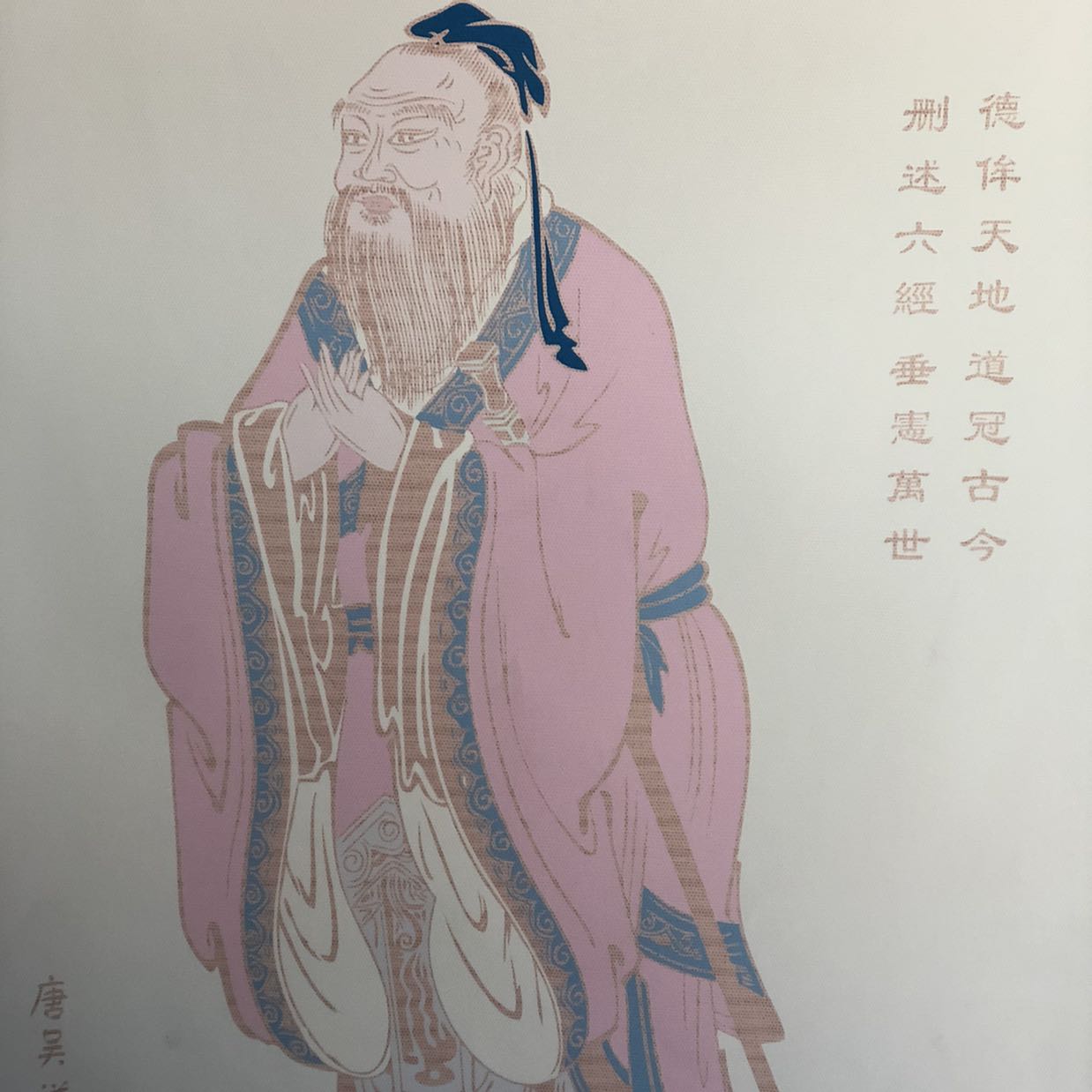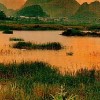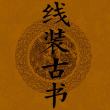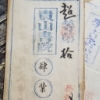博平仰山书院漫谈(下)
六、书院的变迁(下)
据彭熙文所撰《临清州学政张公墓志 》,张建桢曾主讲博平仰山书院。张建桢,字子幹,号芋农,博平大刁村人,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科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临清州最后一任学正。此外他还先后主讲过长清石麟书院、武城弦歌书院、高唐鸣山书院、东阿谷城书院、沂州琅琊书院、沛县湖陵书院等多所书院,编撰有宣统二年(1910)《茌平县志》 ,寿八十二岁,无疾而逝。由其所撰写的《傅鸿诰墓表》和《李宫李墓表跋文》石刻现在均完好保存在仰山书院碑廊内。
张建桢《李宫李墓表跋文》中提到了博平训导宋其端(伯庄)(1848—1915),我不禁想起族谱中关于我曾祖的记载。曾祖世泽公,“字润卿,号恩波,光绪乙未(1899)岁试邑庠生,癸卯(1903)科试一等补增,丁未(1907)训导宋(其端)举优生。宣统己酉(1909)科制钦赐六品顶戴孝廉方正。”即我曾祖世泽公读书问学、取得功名,与仰山书院和宋伯庄先生都有关联。族谱还记载,我曾祖的三伯庆平公“字春华……胞侄世泽七岁失恃,饮食教训二十余年至于入泮,宣统己酉(1909)制科以优增生名附孝廉方正骥尾。博平训导宋其端表以‘训比康侯’匾。”也就是说我祖上的庭堂中还曾非常容幸地悬挂过这位“不啻与郑板桥氏相上下”的书法名家所授的匾额。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全国书院统一改为学堂,书院名称就此结束。民国时期,博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设在这里。1947年间,我大伯乌汝玉(乌林)及族伯乌汝明在此求学时,曾协助商恺(1922-1998)编辑博平县委机关报纸《博平群众》。1948年,商恺离开博平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后调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原仰山书院部分房舍一直作为西街小学的教室和办公用房。
2008年再次重修后,成为“博平镇仰山书院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目前,这里有清代建筑风格的藏书楼、民国中西合璧风格的教学楼、古碑刻碑廊、仿古戏台、门球场及文化综合服务楼等文物展示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成为展示博平人文历史、服务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近日,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的2024年山东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评选中,博平镇仰山书院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被评为“最美基层文化空间”。
七、结语
我把目光和思绪收回到仰山书院藏书楼前,一进大门就能看见的古槐上。看着它,我不知为什么立即就会想起郁达夫《故都的秋》中北国的槐树,想起鲁迅抬头在密叶缝里看一点一点的青天,想起王北山先生的槐轩和他的诗文。在跨越蛇年春节写作的十多天中,我反复查阅了自己收藏的多种地方史志、文史书籍和相关资料,与数位师友进行了探讨交流,新的疑虑和困惑、新的发现和感悟,相互交织,接续不断,一直到现在……漫谈终可以画上我自己认为还算满意的句号。最后,我把自己难以言表的感觉和收获,借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
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