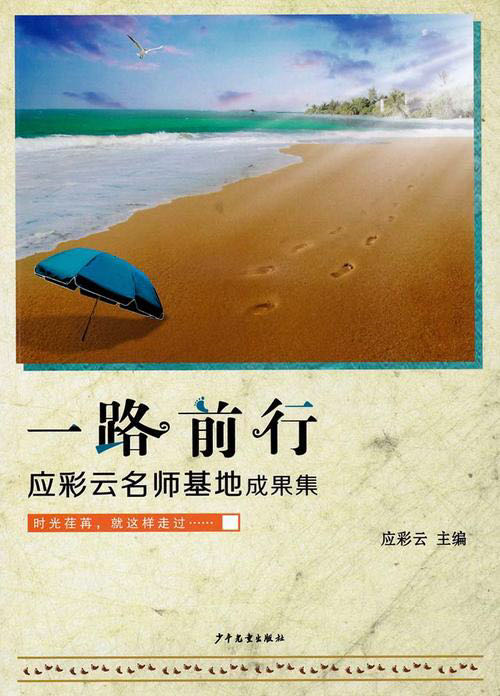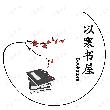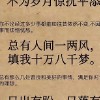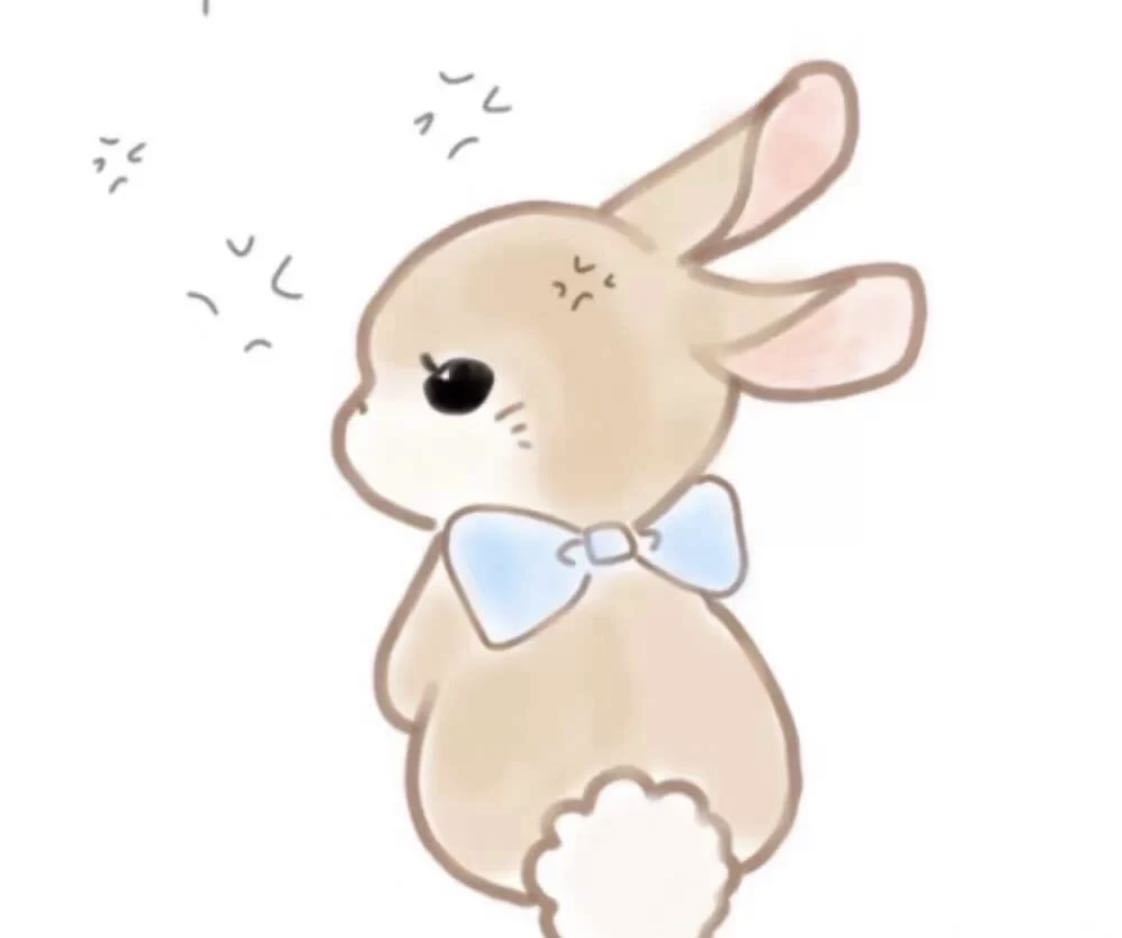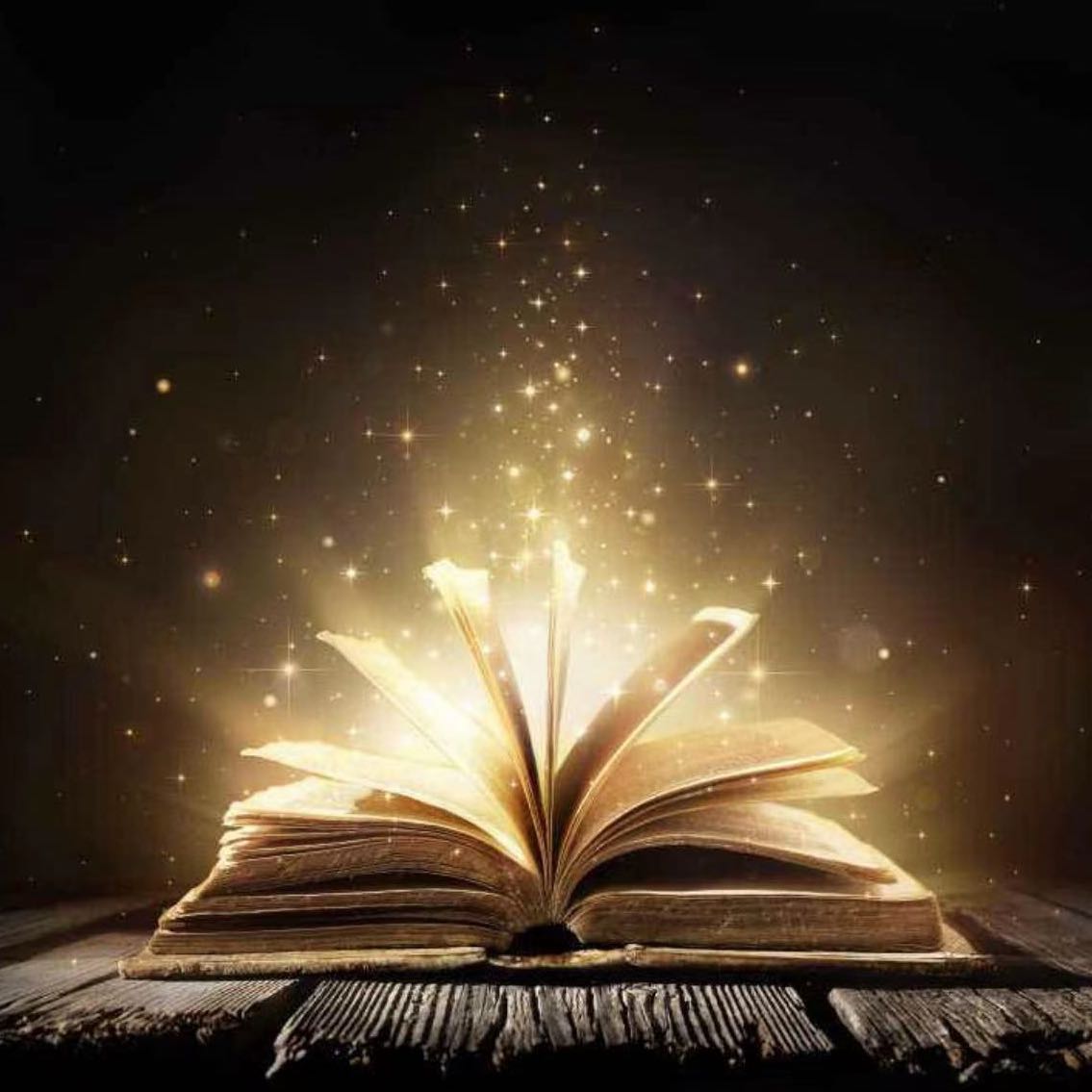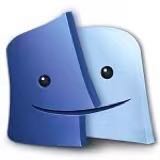再读刘震云老师《一句顶一万句》有感:永爱去浇灌你的孩子
#读过次数最多的书# #读过次数最多的书# 二零一八年这个时候,本人通读了一遍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由于生活阅历和知识背景所限,虽略略觉得该书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找对了人,说一句就够,没找对人,说一万句也没用,其他更加深刻的体会谈不上。一晃六年过去了,这六年,本人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一个简略的通读,对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专题研究和揣摩,对宋明理学的一些语录也读过一些,对中西哲学差异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比较研究,更主要是本人小家庭遭遇变故,本人大家庭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此背景下,面对书架上几十本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决定挑选出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进行重读。这次读得不急,小孩不在身边,不用陪伴,这样我就白天读书,晚上游泳,饭也不用做,直接吃食堂,花了四天时间终于读完,故利用现在空闲时间把读后感写一写。再读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给人的感觉是,人啊活在世上,不但累和苦,还真孤独,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都找不着。以杨百顺为例,他从事过的劳动有(不是职业,也不是工作,职业和工作是资本主义分工背景下的产物)做豆腐卖豆腐、杀猪(杀猪之前想跟着老裴剃头)、染坊挑水、破竹子(破竹子之前想信教骑自行车)、街道上挑水、县衙种菜、入赘做馒头卖馒头,可以说没有停过一下;他用过的名字有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每用一次新名字,就是一次身份的转换,那是真苦啊,没有重大变故谁会愿意改变自己名字,就像古典评书所言,“老子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英雄谁会改变自己名字,可杨百顺不是英雄,是个百依百顺的小老百姓,小老百姓要活着,没有比活着更加重要的事情。小说更多的内容我就不介绍了,看长江文艺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的印刷数量,加上不少人选择阅读电子书,估计阅读过《一句顶一万句》的人至少在500万以上,估计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三以上都阅读过该书,现在直接评论,不做内容介绍。本文认为,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在思想上就是对农耕文化的批判,对比陈忠实老师的《白鹿原》,陈忠实老师的《白鹿原》是对农耕文化的寻根。虽然在人物塑造上,《白鹿原》书中的人物会更容易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个人物印象是他者的印象,也就是说,你看的是别人的故事;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说的是自己,那个人物印象看似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那是观众没有看懂,看懂了,就会觉得杨百顺也好,其他人物名字也好,那是你自己的化名,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随着时间的沉淀,以后会越来越出名,甚至未来可以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进行媲美(当然思想高度和深度不能和《狂人日记》相比)。以本文作者的阅读观感而言,本人看到的是在一片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地处黄河边沿地带的广阔盐碱地,这种土地由于不肥沃,就诞生不了(养不起)千年古镇,没有千年古镇,就缺乏在当地世代守卫的名门世家(名门世家世代守卫的就是道德伦理,也就是要能装,能装要用本钱,你没有本钱拿什么资格去装),所以当地人给人的印象不但脑子活,为人处世方式还滑,实用主义至上,你不活也不滑就无法生存,就会淘汰,要不远走他乡,要不会给父母选择性淘汰(不给你娶老婆),或者给兄弟竞争性淘汰(变相抢夺你的家产)。在这样的地方,由于是平原,村子和村子之间的差异就不明显,或者说,地理坐标就不明显,因为没有大山、丘陵、河流等标志,使村子之间拥有立体地理差异,村子之间只有大小的平面差异,而没有高低的立体差异。同样,在一个村子内部,房子与房子之间也是千遍一律,人多就五间房,人少就三间房,孤老就一间房,甚至房无半间,地无一亩。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看到的就是人,看不到自然,因为自然都一样,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盐碱地,所以不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有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也没有多少描写延津自然景观的文句。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因为没有自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卷,就会缺乏个体的主体性,没有个体,只有个人,因为个体是独立的,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要做给被人看的,哪怕装也要装,不装就混不下去,吴香香和老高跑了,所有人都要逼得吴摩西带着巧玲去寻人,没有这个寻的过程,就无法获得姜虎房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找了,找不着,那是另外一回事。老婆跑了,为什么要找,这就涉及到老婆的物化,或者老公的物化,在吴香香和吴摩西的关系中,作为女人的吴香香是老公,作为男人的吴摩西是老婆,这就涉及到公和婆,或者社会意义上的男和女之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这样的地方,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独立的平等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主从控制关系。对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夫妻关系是一场以爱的名义进行的对等控制关系,当然了,这种控制不是直接对人的控制,而是通过物(财产)的中介所完成的控制,比如男性通过拥有财富的多少把自身物化,与女性通过拥有的美貌也把自身物化,物化与物化之间进行公开的等价交换。但在这样的地方,夫妻之间的关系由于是一种主从控制关系,而且由于物的缺乏,物的稀少,大家都穷得裸搭凳,所以无法通过物进行中介,也就只能进行人对人的直接控制,那就是涉及到夫妻之间的争,如何争,以子女为代价和筹码对对方进行控制和PUA,谁要是舍不得子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谁就必输无疑。本来两个人有话头的,因为又要争那个小家庭甚至大家庭中的主的地位,争了,就会留下后遗症,争的失败方也是暂时的失败,也是口服心不服,这样就会话头越来越少,吃没吃亏心理还是有数的,什么叫吃亏,吃亏就是吃了自己性格软弱的亏,那如果不软弱呢,弄不好就要家破甚至人亡,到了破家这一步,那就变成了理亏,理亏了,就获取不了舆论的支持,那就会影响自己的生存。那这样下去,不贱的人也要变贱,所谓人至贱则无敌,人贱了,就没有原则,没有原则,就没有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就没有道德自律,伦理的他律也会失灵,就会偷和骗,偷到骗到就是本事。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孤独感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人是活在他人的评价世界中,所谓的社会关系就是别人的评价,受不了要不就要躲避,要不就要逃跑。父子之间的亲也是名义上的亲,父子之间的孝也是做给被人看的,夫妻之间的亲也是客厅的亲,到了卧室就不亲,到了床上,做事也是完成任务,要播种生产嘛。因为缺乏不二神,人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会行为短期化,尽快变现,所以这种地方偷骗盛行,偷骗可以在内部偷骗,也可以去外部偷骗,因为这种地方的人脑子活行事滑嘛,那抢呢,抢就不一定,要抢也只能在家庭内部抢,抢别人的弄不好会打扁了头,什么叫家庭内部的抢,父母抢子女的,子女抢父母的,兄弟抢兄弟的,兄弟抢姐妹的,丈夫抢妻子的,朋友之间只能骗,不能抢,可以借刀杀人,不能上门明抢。在这样的地方,只有相对是非,道理也是个理,今天是这个理,到了明天过了一夜,就变了一个理,对这个人是这个理,换了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理,所以人卷啊,活的累啊,甚至心苦啊,能找上一个说话的人那就多高兴啊,但是,即使找上了一个能说话的人,必须离开这样的地方,不离开的话,说上话的迟早也会变得说不上话。比如,吴香香和老高能说上话,所以要离开,去开封火车站讨生活,牛爱国和章楚红也要离开,才有可能在一起,庞丽娜和老尚也要私奔,什么叫私奔,私奔就是脱离以前社会关系的控制,同样也放弃以前社会关系带来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奔就是快速离开,私就是独自决定,谁都不能告诉,连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能告诉,但可以告诉朋友,什么是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的才叫朋友,近处的迟早会变仇敌,因为朋友之间太近了,就会被那些传声筒离间变质,传声筒不传话,嘴就会作痒,那就会憋得慌,那自己憋得慌还不如去看别人的戏。小说中提到,意大利神父老詹在延津传一辈子教,就发展了八个信徒。事实上,像延津这样的地方,由于当地人脑子活,行事滑,这种地方还有其他类似的地方,弄不好就是乌烟瘴气、诈骗横行、道德败坏、是非不分的地方,也就是说,这种地方最缺乏的就是不二神的信仰,老詹要传的那个教,理论上在当地有极大的需求,那为什么才发展了八个信徒呢?这就涉及到致富问题,赚不到钱,谁也不愿意信教,由此可见,不管是这个教还是那个教,牛也好马也好,要让人信,就要让人富,信仰是有产阶级的事情,无产阶级的信仰是功利性和目的性很强的信奉,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为了原则不但可以牺牲金钱,甚至生命。我们再看老詹的遗物,那是一座拥有七十二扇窗户的大教堂图纸,为什么叫七十二,孙悟空七十二变,七十在西汉以前就是很多、非常多、多得不得了的意思,四十二加二十八等于七十,二十八是星宿,四十二是六乘以七,在中国道家文化中具有少生多的繁殖复制的含义。老詹在图纸上留下了“恶魔的私语”,为什么叫“恶魔的私语”,那是失望啊,在老詹眼中,他所见的那些人都是不信神的罪人,都没有是非啊,可就是那些人,还经常讥笑老詹一无所有,既没有家,连老婆都没有一个,活在世上就是彻底的失败,可据闻,老詹原型妹妹的孙子,后来成为了意大利米兰地区的大神父,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差异得有多大的鸿沟啊。再看吴摩西在图纸上留下的“不杀人,我就放火”,“杀人放火”是中国文化中的针对私人的大罪,仅次于谋逆造反罪。可事实上,吴摩西处处受到他人伤害,哪怕他在心理上杀人一万次,他最终也没有杀人放火,他选择了逃避,远离那个让他心不安的是非之地,在去宝鸡找老汪无果的前提下,最终选择了在咸阳成家落户,哪怕他跟他的老婆子聊不来,跟子女也聊不来,但还是跟一个孙子聊得来,吴摩西(罗长礼),吴摩西改名罗长礼,背叛了中国文化“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祖宗崇拜精神,但是,哪怕没有话说,他还是选择了成了一个家,而没有选择一辈子去寻找那个能说上话的巧玲,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孙子罗安江和他能说上话,回到了中国文化的隔代亲漩涡中去了。应该说,老詹是有使徒精神的,杨摩西的使徒精神最多只有一半,曹青娥(巧玲)是生活中的智者,巧玲既不幸也是幸运的,她的亲妈吴香香沉迷于自己的欲望,是个自私的人,哪怕在中国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爱,不是说父母可以为子女做什么,而是父母可以为子女不做什么,从这点而言,吴香香为了跟老高私奔,偷偷回来收拾细软,但是居然抛下女儿,说明,在她心目中,细软比女儿重要,有了细软还可以再生孩子(事实上后面也很快怀孕了),但是带着孩子会花掉细软。后来巧玲经过几次变卖,老尤卖她得了十块大洋,第一个人贩子比较专业,十块买来巧玲,卖给第二个不专业的人贩子,卖到了二十块大洋,第二个人贩子因为不专业,把巧玲卖给老曹夫妇,才得了十三块大洋,除掉吃喝不算,还倒贴了七块大洋。老曹夫妇是爱巧玲的,因为他们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对巧玲的爱比很多亲生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深厚,所以,曹青娥的生活智慧也是吴摩西、老曹夫妇用爱浇灌出来的,没有得到爱的浇灌,怎么能有生活的智慧呢,自顾都不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曹青娥这么跟她的二儿子牛爱国说过,罗安江的遗孀何玉芬也这样跟大表弟牛爱国说过,最终,他们的言语让牛爱国抛下了对章楚红过往经历的心结,章楚红名字也起得有意思,一个率性而为随心而动的丫头片子。总体而言,《一句顶一万句》描述的都是社会中庸碌劳碌的普罗大众,就是告诉大家,再大的苦都不算个事,不要太认真,也不能太认真,认真也没用,老詹一辈子认真传教,也就发展了八个信徒,这点,该书和余华的《活着》有点类似。关于人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中,主体性是大人物的事情,比如,一个小村庄受了隔壁人多村庄的欺负,一般不会反抗,他们会这样说,“还不是因为我们的村庄没有出人”,他们所谓的“人”就是那种“大人物”,或者当了大官,或者发了大财,或者出了参透了生死或脱离世俗的亡命之徒,一个小村庄真出了土匪,估计隔壁的大村庄在欺压这个小村庄之前都得反复掂量掂量。那么,通观《一句顶一万句》整部书,有没有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去证明了自己的主体性呢,或者说,通过努力,一步一步蜕变,最终由弱者成为了强者的个案呢,似乎没有,弱者要证明自己的主体性,要造衙门的反,造世俗观念的反,造舆论的反,而且要直面问题,不得采用那种借刀杀人、秋后算计的智谋,那就要敢打架斗殴,甚至敢杀人放火。没有,好像还真没有,巧玲的生父,姜虎在山西劝架,结果被一个山东人拿刀杀了,那两个挑起事端的姜虎老乡,老布和老赖,看到山东人跑了,也没有第一时间提刀去追人,说明他们也就是过个嘴瘾,到了真处还是胆小如鼠,由此看,河南人还是没有山东人胆大。泼皮倪三,祖父是前清举人,做过知府(正厅级干部),父亲败完了家业,现在就只能靠耍无赖过活,动不动就拿着一根绳子要到别人家上吊,似乎也不是真正的英雄,其实啊,他能闹也只是在延津能闹,因为他们家族在延津有庞杂的裙带关系,谁要是真把倪三打死了,倪三的亲戚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毕竟他从事的就是小偷小摸的小恶,再说了,倪三欺负的都是那些小生产者、手工业者,这些人具有小微阶级的天生软弱性。最后,重点谈下说得着和说不着的问题。在农耕文化中,由于农耕文化离不开土地,受制于牛耕的耕作方式,土地的耕作半径有限,人和土地就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交往的空间范围有限,交往对象也有限,导致人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通过繁忙劳动而形成的养活与被养活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将就的共同劳动关系,共同劳动嘛,还要抚养子女,哪有那么多话说,天天说话,哪谁帮你去劳动,所以,在小家庭中(生产的基本单位),说不上话是常态,不但夫妻说不上话,连父子也说不上话,甚至母子也说不上话,日子就在天天争吵中过,正因为有争吵,争什么,吵什么,还不是为了一口气,为了一口气,就要争气,争气争气,就会激发人的斗志和主观能动性,那就增加了生存的机会。在大家庭中,由于掌握了特定的大型生产资料或者连片或者配套的生产资料,可以获取超额的级差地租或者垄断利润,就可以对他们家的女性进行更大的经济压迫和性别控制,还可以养几个小老婆,这些女人之间为了争宠吃醋,会变着花样百般讨好,或者先把自身进行物化和异化,由于和主人不存在平等的关系,所以会过得更加心累,当然了,她们可以在更加贫穷的妇女们身上展示自己的花花绿绿的裙子,以显示自己的富贵和幸福。那么,农耕文化家庭之间,无论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内部成员之间都很难说得上话,那么,什么文化才能说得上话。本文认为,只有游牧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才能说上话,这种社会下的个体是流动的,游牧文化下的牧场是可以自由放牧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那是契约社会,不是人身依附社会。那么,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并没有反思说不上话的社会背景,只是告诉大家,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个就有点佛教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鼓励无条件的宽容和包容,那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社会,因为没有抽象的是非,只有具体的是非,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加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说不上话的悲剧就会代代重演,说白了,还是缺乏对不二神的信仰,正因为缺乏不二神,至于那些土地爷爷都是可以用糖衣炮弹进行收买和贿赂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既没有对文化进行批判,也没有对人性进行反思,无非就是告诉大家痛并快乐着,因为你的苦还没有别人苦,别人都没有说什么,那你就更不能说什么,也就是说,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既没有否定精神,也没有救赎精神,否定精神是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造反,救赎精神是统治阶级的忏悔。当然了,不能要求文学作品鼓吹阶级斗争,那是特定年代的延安文艺精神,或者说,文学、历史、哲学在言志或者载道上到底有哪些差别。本文认为,对哲学而言,她可以提升人——类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世界不完全是自然)的水平,她是假定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不会说谎的个体,谁要是说谎,那就会开除人籍变成畜生,开除球籍扔到外太空去。哲学怕什么,哲学最怕骗子和谎言。不学习哲学,就容易被洗脑。对历史学而言,我们多看点历史学的书籍,会知道英雄们的思维方式,因为历史记载的都是英雄人物,普罗大众的代表也是人类的精华,也是英雄人物嘛,不看历史,就不知道社会的演变规律。对文学而言,那里面有太多小人物的套路,光学习哲学和历史,不学习文学,那就会变成书呆子,被生活中的小人物吊打,还会被人说情商低下。哲学管人的大脑,历史学管人的眼睛和耳朵,只有文学,才能慰藉你的心脏,不学习点文学,不看点小说,就说不来话,说不来话就没有人陪你说话,那就要变成吴摩西,变成牛爱国,摩西传道忘了人还有肉身,没有肉身,你那个道又寄托在哪里?爱国不能忘了爱家,国爱了,家没爱,老婆跑了,你后面又拿什么让你的下一代爱国。总体而言,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难得的不可多见的佳作,唯一就是在思想上不能突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当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作品在思想上能媲美甚至超越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我最大的体会是,一定要从小用爱浇灌孩子,有爱浇灌的孩子,哪怕是收养的孩子,也不会活得那么累那么苦。可在我们东方氏族社会,一无私有制,二无人身自由,三无财产自由,四无契约精神,不活得累不活得苦也比较难,那就尽量救自己吧。我们既没有不二神,现在又打倒了皇权,降服了强龙,那些地头蛇都蠢蠢欲动,说不上话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所以啊,做人苦啊,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尤其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