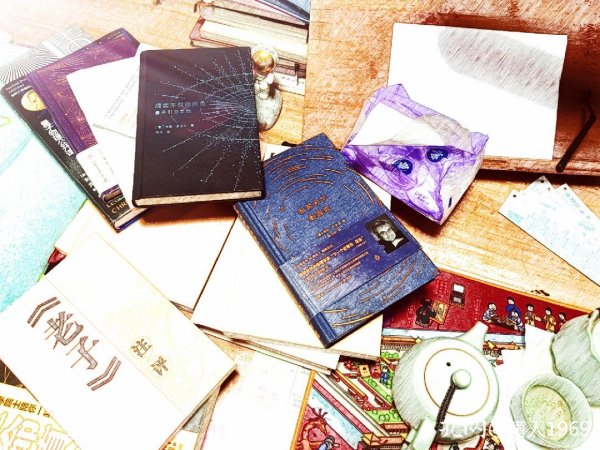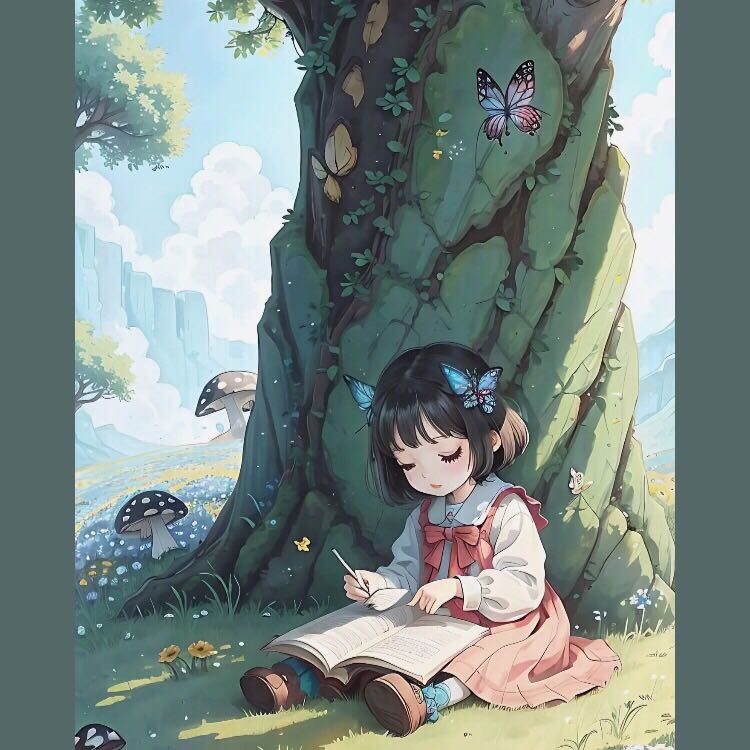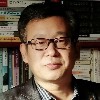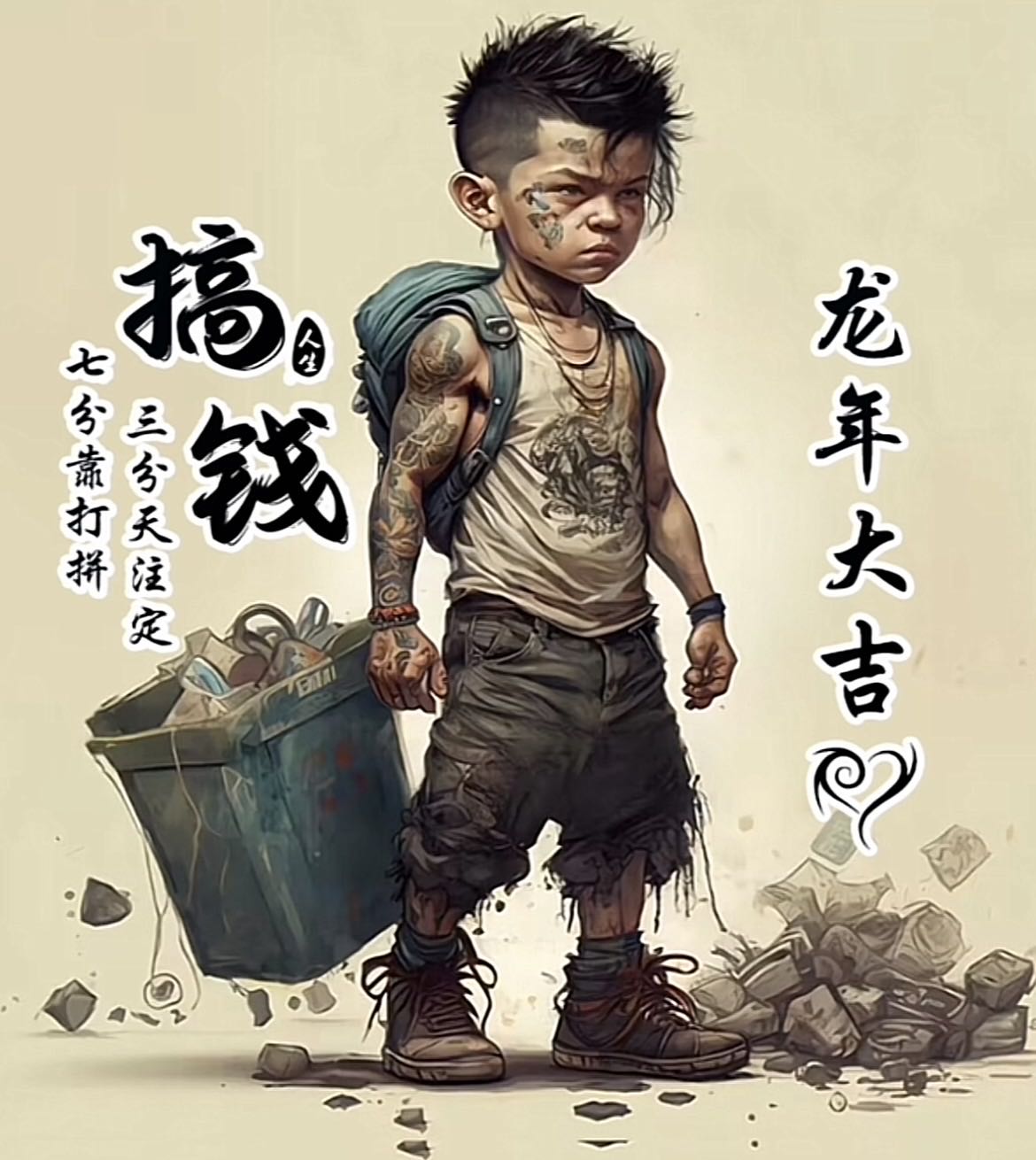造化是个辩证法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
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鬼使神差。贾谊没想到,他两千多年前的喟叹,却让后世的一个呆子纠结了好多年。天地和万物肆无忌惮、没心没肺地存在着,可造化在哪儿呢?阴阳又是什么呢?
纠结时不时把目光拉向星空,拉向地平线,也拉向哲人们穷究的天人之际。
能让呆子开窍,并把上帝最深层的秘密展示出来的,大概只有黑格尔了——这个将古典哲学带到最高峰的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童话作家”(我是第一个发现的)兼最大的形而上学家。
老黑说,创世的不是上帝,而是蹦蹦跶跶的爱好画圆的思辨,逻辑是维持宇宙秩序的警察,理性是把禁锢在个别性当中的普遍性解救出来的侠客。精神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酒神,自然是它的小酒馆,在里面花天酒地、“一味开怀嬉戏”。
绝对是世界的本源,一个被不满情绪支配的永恒的叛逆者。当一股否定性的力量意识到某个恰当的理念(精神),这个理念就把这股力量从母体绝对中外化出来,展开一个新的现实:一个实体、一个存在物。黑格尔说,实体即主体,每一个具体的存在物,同时是一个拥有特定精神的主体。
获得实体的理念就是绝对理念,也称为绝对精神。精神以实体的方式回到了绝对自身之中,绝对也成长为绝对精神。绝对不会满足现状,会将这一过程不断进行下去。后续过程都是在前面过程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起来的。绝对精神的形状,是螺旋上升的一个个圆圈。
什么样的精神(理念)是恰当的精神,能从绝对中异化出来,拥有自己的实体?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老黑说,别看他千变万化,其实就是一个辩证法。
当精神获得实体成为现实,在其自身内部各成分之间以及实体与实体之间,会形成矛盾(因为这些实体都是拥有自我意志的主体)。把现实的意志当成正题,这些矛盾的意志就是对立面的反题,精神的唯一出路,就是运用思辨,综合正题反题,形成一个合题并将之送上王位,创建新的现实。宇宙大戏就在这个底层逻辑的支配下一圈一圈地上演了。
所以,制作万物的造化就是那个否定性的辩证法,正题与反题、现实与理想的互动就是燃烧的阴阳。思辨的理性是唯一的造物主,他麾下所有的现实都是合乎理性的,但同时,所有的理性也都是暂时的。在因其自身“普遍性”不足而生发的反题作用下,终将被扬弃而形成的新的合题所取代。他可以迟到,但不会旷工:“哲学作为有关世界之思,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完成自身,并在那里耗尽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时才起飞。”
精神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从母体中层层外化出来,层层脱嵌,离出发地越来越远。可他每一次成功落地,却又都是因为找到了来时的“依据”——那个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就像寻找祖先的灵位一样,在先的祖先是后世的前提,越老的祖先基础越深,被发现得也越晚。“前进即回溯”,离乡即回家。实体离本源越来越远,主体离本源越来越近。
绝对外化自身为绝对精神,是其从自然走向自觉,绝对精神返回绝对,则是由自在走向自为。“这一普遍运动就是精神形成的系列……在发展中必定存在进步,不是朝向抽象的无限性,而是返回到自身。”
当这种发展进步到由人类做他的代言人时,精神的目的——精神的精神——被揭示出来:一个新的精神王位迎来了它的国王——
自!由!
忽然,一段熟悉的旋律向耳边飘来。我知道,那位远方老友想我了: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地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开的思想和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而我,已泪流满面。 ...展开全文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
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鬼使神差。贾谊没想到,他两千多年前的喟叹,却让后世的一个呆子纠结了好多年。天地和万物肆无忌惮、没心没肺地存在着,可造化在哪儿呢?阴阳又是什么呢?
纠结时不时把目光拉向星空,拉向地平线,也拉向哲人们穷究的天人之际。
能让呆子开窍,并把上帝最深层的秘密展示出来的,大概只有黑格尔了——这个将古典哲学带到最高峰的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童话作家”(我是第一个发现的)兼最大的形而上学家。
老黑说,创世的不是上帝,而是蹦蹦跶跶的爱好画圆的思辨,逻辑是维持宇宙秩序的警察,理性是把禁锢在个别性当中的普遍性解救出来的侠客。精神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酒神,自然是它的小酒馆,在里面花天酒地、“一味开怀嬉戏”。
绝对是世界的本源,一个被不满情绪支配的永恒的叛逆者。当一股否定性的力量意识到某个恰当的理念(精神),这个理念就把这股力量从母体绝对中外化出来,展开一个新的现实:一个实体、一个存在物。黑格尔说,实体即主体,每一个具体的存在物,同时是一个拥有特定精神的主体。
获得实体的理念就是绝对理念,也称为绝对精神。精神以实体的方式回到了绝对自身之中,绝对也成长为绝对精神。绝对不会满足现状,会将这一过程不断进行下去。后续过程都是在前面过程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起来的。绝对精神的形状,是螺旋上升的一个个圆圈。
什么样的精神(理念)是恰当的精神,能从绝对中异化出来,拥有自己的实体?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老黑说,别看他千变万化,其实就是一个辩证法。
当精神获得实体成为现实,在其自身内部各成分之间以及实体与实体之间,会形成矛盾(因为这些实体都是拥有自我意志的主体)。把现实的意志当成正题,这些矛盾的意志就是对立面的反题,精神的唯一出路,就是运用思辨,综合正题反题,形成一个合题并将之送上王位,创建新的现实。宇宙大戏就在这个底层逻辑的支配下一圈一圈地上演了。
所以,制作万物的造化就是那个否定性的辩证法,正题与反题、现实与理想的互动就是燃烧的阴阳。思辨的理性是唯一的造物主,他麾下所有的现实都是合乎理性的,但同时,所有的理性也都是暂时的。在因其自身“普遍性”不足而生发的反题作用下,终将被扬弃而形成的新的合题所取代。他可以迟到,但不会旷工:“哲学作为有关世界之思,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完成自身,并在那里耗尽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时才起飞。”
精神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从母体中层层外化出来,层层脱嵌,离出发地越来越远。可他每一次成功落地,却又都是因为找到了来时的“依据”——那个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就像寻找祖先的灵位一样,在先的祖先是后世的前提,越老的祖先基础越深,被发现得也越晚。“前进即回溯”,离乡即回家。实体离本源越来越远,主体离本源越来越近。
绝对外化自身为绝对精神,是其从自然走向自觉,绝对精神返回绝对,则是由自在走向自为。“这一普遍运动就是精神形成的系列……在发展中必定存在进步,不是朝向抽象的无限性,而是返回到自身。”
当这种发展进步到由人类做他的代言人时,精神的目的——精神的精神——被揭示出来:一个新的精神王位迎来了它的国王——
自!由!
忽然,一段熟悉的旋律向耳边飘来。我知道,那位远方老友想我了: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地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开的思想和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而我,已泪流满面。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