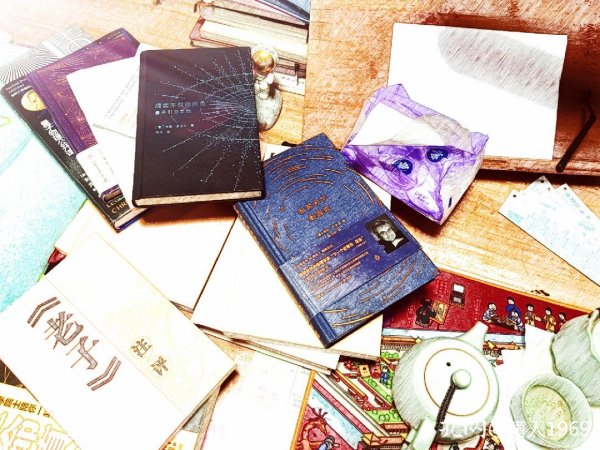道生一,一不能生二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问题来了。
生一的“道”是什么?生完一后,道去了哪里?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还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一、二、三、万物,皆是有形之物,既已定型,何以生成别物?
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借助当今前沿的科学知识了。
通常来讲,经过了几百年的科学洗礼,多数人认为世界是由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组成,物质是能量的高度浓缩,由原子组成,原子由更小的基本粒子组成。
而当科学家们为我们撬开原子世界的大门时,世界图景变了——
那是一个鬼魅幽灵们玩耍栖居的世界,一个让科学家们抓耳挠腮、目瞪口呆的世界:既是波又是粒子的量子、既死又活的叠加态的猫、不受时空影响的纠缠、观察者带来的干涉效应……
总之,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不再是物质,而是事件,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关系、关联、相互作用。微观世界的粒子,只有在相互作用时才现身,没有了相互作用,则消失为一片“概率云”。宏观世界也同样,没有能够单独存在的物理系统,都是在与其他物理系统发生关系时才存在。没有了相互关系,任何物理系统都会瓦解消散。
关联性,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属性。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巨大网络,可感的有形的物理系统,是这个网络的节点。这个网络不断地通过节点调整、收回、投放特定的关联,投射在我们感官中,就是以物质形象呈现出来的物理系统的生灭变幻。
那么,关联是什么呢?又是谁主导了这些关联呢?当我们提出关联、关系、相互作用这些概念时,依然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的观察描述。而这些客体既然能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他们就需要有感知能力和共同渴望,而且能够以某种方式去追逐或实现这种渴望。所以,这些客体是具有主体性的。
何不扇动想象的翅膀,让世界开口讲述一下,在为我们呈现这些现象时,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发生了什么?
世界是从一团原始、混沌、散乱、热情的“汤”中,开启其演化征程的。狂野躁动的能量背后,是一个个被焦虑与渴望的情感裹挟着的“精神”们,他们渴望着“换个活法”,摆脱困境。于是,将精神秩序化的“道”,扯起一杆“逆天改命”的大旗,开始招兵买马了。
道,是基于共同渴望下的共同想象,能从原始的“汤”中召唤出一部分离散的精神们,建立关联,开辟出有序。这种关联需要由物质搭建起特定的空间结构,作为“道”的身体,同时也是展示给其他精神主体的“语言”。这就是宗教所说的“道成肉身”。第一代基本粒子的出现,“道生一”了。
生一的道,在固守自身的同时,作为一个新的精神主体,依然渴望被一个更高的“道”秩序化,这个新的道被悬设出来,”道离肉身”了。当这个悬设的道被其他精神主体渴望到,两者便结合在一起,一个新的结构新的肉身——“二”,立于世间了。所以生“二”的不是“一”,而是融合了“道一”的“道二”。这种过程在时间中持续展开,三、四直至万物,一个存在巨链,一个关联网络蔓延开来,轰轰烈烈地跟随着“道”,一起奔赴在没有终途的朝觐的路上。
世界是精神判经研典、著书立说的道场,所有的现象都是道的言说。每一片雪花都是召唤水分子的神庙;每一场季风,都是气体们的集体舞蹈。每一片叶子,每一粒尘埃,每一次晨曦,都是原始精神里长出的浆果。基因是精神创造的最伟大的巫师,它从自然当中获取“信徒”,并为不同的“信众”提供不同的“图腾”,将各自不同的“道”融合关联成一个统一体。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图腾号令起来的物质结成的复杂结构。生命的终结,不是物质和原始精神的消失,而是凝结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图腾、道的消失。
“世人谓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行文至此,有人会说我狂人呓语、痴人说梦了。无妨、无妨,没有金刚护体,岂不怪力乱神?我有重量级大咖助阵:
“所有物质,都来源于一股让原子产生运动和维持紧密一体的力量。这股力量的背后是意识,是心智,是一切物质的基础。”——普朗克
不知道普朗克是谁,可以找度娘。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问题来了。
生一的“道”是什么?生完一后,道去了哪里?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还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一、二、三、万物,皆是有形之物,既已定型,何以生成别物?
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借助当今前沿的科学知识了。
通常来讲,经过了几百年的科学洗礼,多数人认为世界是由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组成,物质是能量的高度浓缩,由原子组成,原子由更小的基本粒子组成。
而当科学家们为我们撬开原子世界的大门时,世界图景变了——
那是一个鬼魅幽灵们玩耍栖居的世界,一个让科学家们抓耳挠腮、目瞪口呆的世界:既是波又是粒子的量子、既死又活的叠加态的猫、不受时空影响的纠缠、观察者带来的干涉效应……
总之,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不再是物质,而是事件,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关系、关联、相互作用。微观世界的粒子,只有在相互作用时才现身,没有了相互作用,则消失为一片“概率云”。宏观世界也同样,没有能够单独存在的物理系统,都是在与其他物理系统发生关系时才存在。没有了相互关系,任何物理系统都会瓦解消散。
关联性,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属性。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巨大网络,可感的有形的物理系统,是这个网络的节点。这个网络不断地通过节点调整、收回、投放特定的关联,投射在我们感官中,就是以物质形象呈现出来的物理系统的生灭变幻。
那么,关联是什么呢?又是谁主导了这些关联呢?当我们提出关联、关系、相互作用这些概念时,依然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的观察描述。而这些客体既然能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他们就需要有感知能力和共同渴望,而且能够以某种方式去追逐或实现这种渴望。所以,这些客体是具有主体性的。
何不扇动想象的翅膀,让世界开口讲述一下,在为我们呈现这些现象时,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发生了什么?
世界是从一团原始、混沌、散乱、热情的“汤”中,开启其演化征程的。狂野躁动的能量背后,是一个个被焦虑与渴望的情感裹挟着的“精神”们,他们渴望着“换个活法”,摆脱困境。于是,将精神秩序化的“道”,扯起一杆“逆天改命”的大旗,开始招兵买马了。
道,是基于共同渴望下的共同想象,能从原始的“汤”中召唤出一部分离散的精神们,建立关联,开辟出有序。这种关联需要由物质搭建起特定的空间结构,作为“道”的身体,同时也是展示给其他精神主体的“语言”。这就是宗教所说的“道成肉身”。第一代基本粒子的出现,“道生一”了。
生一的道,在固守自身的同时,作为一个新的精神主体,依然渴望被一个更高的“道”秩序化,这个新的道被悬设出来,”道离肉身”了。当这个悬设的道被其他精神主体渴望到,两者便结合在一起,一个新的结构新的肉身——“二”,立于世间了。所以生“二”的不是“一”,而是融合了“道一”的“道二”。这种过程在时间中持续展开,三、四直至万物,一个存在巨链,一个关联网络蔓延开来,轰轰烈烈地跟随着“道”,一起奔赴在没有终途的朝觐的路上。
世界是精神判经研典、著书立说的道场,所有的现象都是道的言说。每一片雪花都是召唤水分子的神庙;每一场季风,都是气体们的集体舞蹈。每一片叶子,每一粒尘埃,每一次晨曦,都是原始精神里长出的浆果。基因是精神创造的最伟大的巫师,它从自然当中获取“信徒”,并为不同的“信众”提供不同的“图腾”,将各自不同的“道”融合关联成一个统一体。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图腾号令起来的物质结成的复杂结构。生命的终结,不是物质和原始精神的消失,而是凝结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图腾、道的消失。
“世人谓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行文至此,有人会说我狂人呓语、痴人说梦了。无妨、无妨,没有金刚护体,岂不怪力乱神?我有重量级大咖助阵:
“所有物质,都来源于一股让原子产生运动和维持紧密一体的力量。这股力量的背后是意识,是心智,是一切物质的基础。”——普朗克
不知道普朗克是谁,可以找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