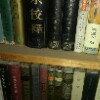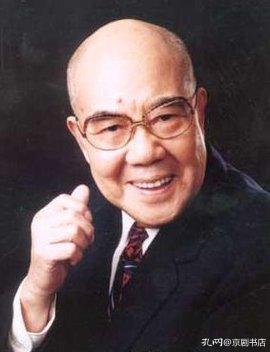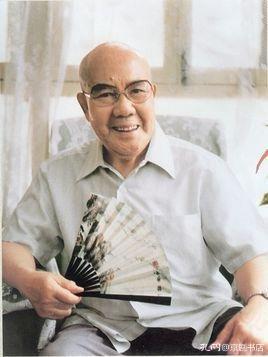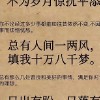![]()
#访古记# “文”期间,谢虹雯的母亲碧云霞在珠市口的一家油盐店里看到张君秋买咸菜,心里油然生出一种凄凉感,回到家里便对谢虹雯说到此事。这么大的角儿,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何曾沾过他的手?
当初谁能想到张君秋会落到这个地步!娘俩商量了一下,决计当天晚上去看看张君秋。进了棉花四条的张君秋家门,一进门就是一张用砖搭起的床--一块门板,老太太躺在床上,张君秋就同娘一起睡在这块门板上。谢虹雯目测一下,门板不过一人多长一点,放下枕头一躺,兴许双脚还搭在门板外面。
老太太糖尿病,还吐血,这样的条件对病人、对全家人都不好,张君秋只是叹气,没办法。谢虹雯说:“不行就把老太太接到我们红土店居民楼去。红土店居民楼有个放杂物的地下室,收拾收拾放张床也比这儿宽裕。我住在楼里头,楼里头还有亚萍和她的妈李婉云住,都不是外人。老太太有我们两家照应着,你该不会不放心吧?”
张君秋忙不迭地轻声告诉谢虹雯:“我可是'黑帮'呀!居委会不准收留'黑帮'的家属啊!”那神情让人觉得又好笑又心酸。谢虹雯说:“我不知道什么'黑帮'不'黑帮'的,我只知道这是个生病的老太太。再者说,我在红土店就是搞街道居委会工作的,这主意我还能拿。”张君秋的心里不住地念阿弥陀佛。
没过几天,红土店的地下室收拾干净了,谢虹雯同薛亚萍一道把张秀琴接到了红土店,两家人一直把老太太伺候到去世。
张君秋忘不了谢虹雯在关键时刻帮的这个忙,逢人提起这件事便说:“她这是救了我的命!”张君秋、谢虹雯没有年轻时代那种罗曼蒂克的浪漫史,谢虹雯佩服张君秋的本事,张君秋佩服谢虹雯的为人,遇事果断,头脑清楚,办事麻利。患难时期互相扶持,这便是他们两人的爱情基础。一九七四年,张君秋与谢虹雯结为伉俪。 ...展开全文
#访古记# 宋宝罗展现风采的时候,正是民族多难时节。江湖夜雨,飘摇寄身。
在东北地区演出,碰上日伪拉壮丁。连夜逃走,戏箱在车站被查出,宋宝罗靠随身携带的一小箱画笔,冒充画画的得免。艺术又阴差阳错救了他。
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暗无天日。宋宝罗多年积蓄买下的房产被当做伪产充了公。没地儿说理去。
旧社会,跑班唱戏必须得拜码头。地痞流氓横行不说,当政的官员,这个“司令”,那个”军长”,也都是些胡传魁式的军阀。一次和妹妹搭班去南通演出,要去拜山。有人告诫宋宝罗:拜客时千万别带着你妹妹去。刚有一位女演员,就被他们给糟蹋了。
警察也人见人怕。敲诈勒索不给,能往你戏箱里倒黑油,让一箱子行头全报废。据说,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从天津回北京,从来不敢从东火车站下车,往往在城外丰台下,然后乘汽车进京。程砚秋就在火车站挨过打。
有时候”码头”多得难以想象:有一次到南京演出,三十六拜都拜了,演出前光戏票送了五六百张,可还是把电灯公司给落下了。当晚《失空斩》,诸葛亮轻摇羽扇刚出来,电灯全灭了。一晚上没电,只能全退票,有什么办法。
”解放后,再也不用担心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了。从那时起,我真心拥护共产党。”宋宝罗说。 ...展开全文
#访古记# 李蔷华人生的改变,是因为继父的出现,李宗林是个学问人,与名家高华、言菊朋等一起拉弦。于是培养她唱青衣,继父也是李蔷华艺术的启蒙人,而且当时重庆赵荣琛重要的演出,父亲都被邀操琴。
1941年李蔷华12岁在重庆看了赵荣琛演出后,一下就被程派艺术巨大魅力所吸引,从此下定决心学习程派。有眼光的父亲请了技术艺精湛、堪与四大名旦比肩的徐碧云先生在上海,给蔷华教基础戏,打下了非常过硬功底。到了1945年底,李蔷华就能与顾正秋等同台演出了。
#访古记# 作为一位允文允武的程派著名青衣,李佩红不仅是中国戏曲学院第二届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还曾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和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要奖项。原本可以自己带徒的她,却在艺术生涯的关键时候选择了拜师继续学艺。
她说:“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京剧艺术真的是博大精深,一个演员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去不断学习。也有朋友劝我,希望我休息一下,但是学无止境,我必须继承老师们对京剧事业的执著,才能奉献出最好的艺术。作为戏曲演员,我们站在前辈艺术家的肩膀上,理应看得更远,对演传统戏思考得更深:怎样演才能让老戏不老,怎样通过再雕琢让老戏重新焕发出经典艺术的光芒,怎样用以情带腔、以腔抒情的程派演唱艺术来吸引当今的观众......”
#访古记# 刘春爱11岁考入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由桑红林开蒙,后被骆玉笙看中,从此跟随骆学习。
由于她嗓音宽厚,天资聪颖,颇受乃师喜爱。在骆先生的精心培育下,很快就学会了骆派代表曲目《红梅阁》、《汜水关》。而后骆老将大部分自己京韵大鼓曲目手把手地传授给了她。
1962年举办的第一届津门曲荟上,刘春爱演唱了由沈鹏年改编《祭晴雯》受到好评,当时《新晚报》上刊登评论文章中称赞其演唱“嗓音甜润、韵味十足,颇具乃师风范,是一个好苗子。”
#访古记# 众所周知,马长礼学马、宗谭是其正宗的看家本事,可他偏偏又特别喜爱京剧老生另一著名流派“杨(宝森)派”。“杨派”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成熟于50年代初。其主要成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特色的行腔儿与演唱风格,通俗地讲是由谭(鑫培)腔儿徐徐切入,自余(叔岩)腔儿一气而出,扬长避短进行二次艺术加工所创造的一种新成果。其行腔吐字力求稳重苍劲,不浮不飘,被行家赞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马长礼对此感触颇深,因而有这样一番对杨派的深刻评述:“马、谭、奚、杨四位名家都先后教过我,马、杨两家对我影响最大。虽然我以较多精力继承马派艺术,但对杨派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忘怀。像老戏《伍子胥》《空城计》《捉放曹》《李陵碑》等我都是宗法杨派路子来唱的。”正是杨派这种独特的令人回味的艺术风格,令马长礼先生一直十分痴迷。
#访古记# 李斯忠的舞台生活的开始,他家里很穷,从小就没有了父亲,因生活窘迫,他在八岁那年就给地主牧羊。虽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对戏剧非常喜爱,白天牧了一天羊,到夜晚还要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看戏。
因为李斯忠那时年龄小个子低,在台下看不见听不清,常爬到马脚上(即高台两旁)聚精会神地去看人家演唱。如果唱的词句稍有不清,他心中就很烦,因为他想学几句,到牧羊时好唱着玩。这个时期,李经常在牧场上乱唱一气“独台戏”。
邻居常说“这孩子的腔真好,要是学戏,将来也能唱份好戏”。这些说法给李斯忠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学戏的信心和决心。
所以在十五岁时,李斯忠就入了科班,每天喊腔跑圈。不久老师就念给他“铡赵王”中包公的词,第二个又念给他“司马貌过阴”中司马貌的词。在学的时候,我感觉司马貌的遭遇,是与我当时所处的社会没有什么区别的。那时我也不知啥叫体会角色,但我同情司马貌,总感觉比演其他的戏用力气。这出戏接连演了三四年,到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展开全文
#访古记# 1978年,邓小平同志路过成都,要求看川剧。2月1日晚上,蓝光临与杨淑英等川剧名家在金牛宾馆演出了传统折子戏《李甲归舟》。当时,蓝光临并不知道为哪位首长演出,直到大幕拉开,灯亮了,才有声音从前面传来:“是邓小平同志”蓝光临得知是为敬爱的小平同志演出时,十分高兴,演出时格外尽心,他与杨淑英配合默契,声情并茂,赢得满台掌声。
当晚演出了4个折子戏,看得台下的小平同志非常满意。表演结束后,他亲自上台同蓝光临、杨淑英等演员一一亲切握手,给演员们以巨大的鼓励。小平同志连看了13个折子戏,都很满意。一个领导同志请示邓小平,对这些传统戏如何处置,邓小平说:“我看过的这几场折子戏,观众可以看,工农兵也可以看,要趁老艺人还在,拍一些资料,要准备一、两台戏,将来可以到北京演出。”此语一出,传统地方戏剧被解禁了更有历史意义的是, “川剧一活,戏剧皆活”,全国300多个剧种闻风而动,出现了一派“劫后余生”的复苏景象。
#访古记# 作曲家朱超伦曾评价海连池:若论海连池老师的表演,莫过他塑造的小苍娃这一角色。海老师刻画的小苍娃,不仅有丑角的幽默,更散发着善良、正义的力量,这也是大家都喜欢这一角色的原因。
海连池老师创立的海派艺术,更是别具一格,我和他不是一个剧种的,但我希望海派的后人们能踏着海老师的脚步,创造出曲剧新的经典。
#访古记# 与许多旧社会的戏曲演员一样,姚澄的家庭非常的穷困,迫于生计,为了让女儿今后能够有好的出路,父亲把姚澄送进了无锡的顾家班学戏,从此便开始了姚澄的艺术生涯。但是起初,姚澄并不愿意学戏,她认为父亲唱戏被人看不起,既不能养家,连自己也顾不周全。
在学戏前的一天晚上姚澄把想法告诉了疼爱她的奶奶,她巴望借祖母的力量能把自己留下来。姚澄回忆说:"我对奶奶说,奶奶,我不去学戏,爸爸学戏也不好,我去学戏也不会好的。又没有钱还被人看不起。
那时叫演员为滩簧婆,我说我不愿意做滩簧婆!后来奶奶说不去怎么行呢,比在家里饿死要好。于是我就去学戏了。从此,姚澄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既有眼泪,又有欢笑,既是卑微,又是光荣,饱含着苦辣酸甜的从艺道路。
#访古记# 欧阳予倩曾评价盖叫天:他不仅是武戏,文戏也有深厚根底,不仅是武生,髯生、老旦他也擅长,可谓是"文武昆乱不挡",可是他从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他孜孜不倦、勤勉力学的精神使他的艺术日新月异。好学、不苟、有恒是他成功的秘诀。
他是个爽直的汉子,表里如一,对待事物情感真挚,只要他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变,曾拒绝为曹锟贿选、张作霖做寿、溥仪纳妃演堂会;敌伪时汉奸重价邀他演《铁公鸡》,他也不去。他勤勉好学,七十岁还和年轻时一样练功,从不间断。他具备着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品质 。
#访古记# 刘长瑜其实本名姓周,而她之所以改随母亲姓刘也是一段历史故事,这与中国的变迁有关。
她于1942年出生,在当时的还没有一夫一妻制的说法,刘长瑜的父亲有三房太太,其中,她的母亲就是三姨太。她的父亲叫周大文,在当时也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据说曾任北平市市长。
不过后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皇姑屯事件,为了保家人周全,她的父亲选择了辞官。虽然辞官,大半生的积累也足够保证这些子女们衣食无忧,而且据说她的父亲和张学良是密友。
后来,刘长瑜演出的时候,张学良还曾亲自到场观看,而刘长瑜之所以能够学习京剧,也与她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在那个社会,很多大富大贵的人家都有欣赏京剧的雅好,她的父亲更是对此达到了迷恋的程度。
他不仅是剧院的常客,在家中也会有事无事哼上两句,这让年少的刘长瑜也对京剧着了迷。作为京剧的铁杆粉丝,她的父亲当然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在发现小刘长瑜的天赋后,她的父母又惊又喜,在刘长瑜刚满九岁的时候就支持她考进了中国戏曲学校。入校的时候,她还姓周,谁知第二年社会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夫一妻制被废除,她没了家。
虽然她的父母已不再是名义上的夫妻,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这种情分怎是随着名义的废除就立刻消失的呢?刘长瑜依然享受着父亲的关爱,但制度就是制度,1961年,刘长瑜在团长的建议下改随母姓为刘。
由她姓氏的变化,体现出整个中国的时代变迁,不仅整个国家在变化,刘长瑜自身也在不断的成长着。自她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后的八年间,她从先后追随于连泉、华慧麟等戏曲名家学艺。
此时的她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并且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京剧人才。 刚入校时,只有九岁的刘长瑜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作为业余爱好的戏剧,竟然会成为今后一生的事业。
她更加不会想到,那个曾经因为发音不标准而被老师批评到半夜痛哭的小孩,有一天能够成为京剧大师。因为过早经历了这些严苛的训练,刘长瑜要比同龄的孩子更为成熟一些,父母对此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心疼。
他们经常会偷偷的在学校门外探望她,刘长瑜有时已经训练的很累了,但还是迅速调整好状态,只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有戏剧天赋这件事一直是刘长瑜引以为傲的,但当她经历过刻苦的训练后,才逐渐明白:
成功只需要1%的天赋,而其余的99%都是用汗水换来的。在学习了八年的旦角之后,刘长瑜这块金子终于发光了,她得到了京剧大师荀慧生先生的青睐,并拜先生为师。
刘长瑜攻青衣、花旦、刀马旦,由于有七八年的花旦功底,她尤其擅长花旦。其实走到这一步,刘长瑜就已经是许多同行中的佼佼者了,她被留在了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当演员。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技巧并赚一些钱补贴家用,她还在戏校兼课。
刘长瑜是幸运的,在成长的路上遇到多位贵人指点,她在团当演员期间,先后得到了雪艳琴、童芷苓、陈伯华等人的指点。甚至豫剧皇后陈素真也曾为她亲身传授技艺。在校期间,刘长瑜多次随团演出,每一次都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让刘长瑜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因为对戏曲发自内心的热爱,刘长瑜在1962年接受了中国戏曲家协会常务理事的任命。作为中国京剧院演员,刘长瑜经常被邀请出国演出,也正是因为有出国演出的安排,险些让她错过了出演《红灯记》的机会。
当时选角的时候,刘长瑜正巧在国外演出。曲素英和张曼玲先后去试了戏,但是领导们总是觉得差了点意思,他们还想再找别的戏剧演员来试一试,直到刘长瑜的出现。
当时,刘长瑜刚从国外回来到农村,是剧院的人极力推荐让她来试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刘长瑜就是那种敢闯敢拼,绝不服输的巾帼形象。领导们由于对刘长瑜并不了解,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刘长瑜往台上一站,双目怒睁,那副精气神完全就是李铁梅本人。
领导们喜出望外,立刻拍板,让她饰演李铁梅。这部京剧在喜剧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下很快就大火了,电影艺术家们瞄准时机,将它翻拍成电影上映。
这样一来,《红灯记》迅速火遍了大江南北。 ...展开全文
#访古记# 袁世海为得到深造,一九四〇年拜郝寿臣为师,技艺更见精益,成为郝派艺术的主要继承人。在此后的十几年演艺生涯中,曾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马连良、谭富英、高庆奎、周信芳、盖叫天、奚啸伯、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新艳秋、李万春、李少春等名家合作演出剧目三百余出。在同各流派艺术家合作演出中,吸取各家精华,博采众家之长,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表演艺术。
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广泛的喜爱,形成了袁派表演艺术的风格体系。
先后搭李世芳的承华社和马连良的扶风社,与李世芳、马连良、李盛藻合作多年。他与李世芳合演的《霸王别姬》,与李盛藻合演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与马连良合演的《四进士》,成一时名剧。
#访古记# 谭富英以谭派嫡系传人的身份,唱法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登上坛台后的唱腔。
马连良的这一段唱,是萧长华编的词。马派登坛后第一句"诸葛亮,站坛台,观瞻四方"就唱一个大腔,而且连着下一句的"我望江北"这个腔才收住。
谭富英则是到"叹只叹,东风起,火烧战船,曹营的兵将,无处里躲藏"这一句才使一长腔,是老腔(裘盛戎在《将相和》中廉颇自我生气的那一句"……教老夫难以安然"即用此腔) 谭富英唱来亦自不凡。
建国以后,二人合作,再演《群英会·借东风》,马连良饰孔明,谭富英饰鲁肃,不再演借东风,记得他有这段唱的也已不多了。 ...展开全文
#访古记# 《锁麟囊》一剧,李佩红出色的唱念,贴合人物命运发展轨迹的不同扮相,表演上将分寸感和技艺展示合理配合的功力等方面都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朱楼"、"大团圆"几场中的演唱、水袖功夫展示出了她在程派艺术方面日益成熟、老到的本事。
10月6日下午的悲剧《荒山泪》也是李佩红得程派名家王吟秋手把手亲授的戏,表演这样高潮不多而重在舞台上下内心沟通的戏,更容易使演员有吃力不讨好之感。李佩红在剧中的发挥则是不断令观众眼前一亮,即便一个小小的叫板起唱念白或者一个不起眼的身段,也会引来观众十分热烈的掌声。至于剧中的几段著名唱段,更是博得行家和观众的盛赞。上海名丑孙正阳(在《智取威虎山》中饰演过栾平)的加盟助演,也令李佩红的戏增色不少。
程砚秋之子程永江、上海越剧名家袁雪芬等观看演出后,对李佩红在程派剧目方面所下深功和多年来的不断提高给予了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