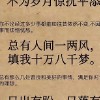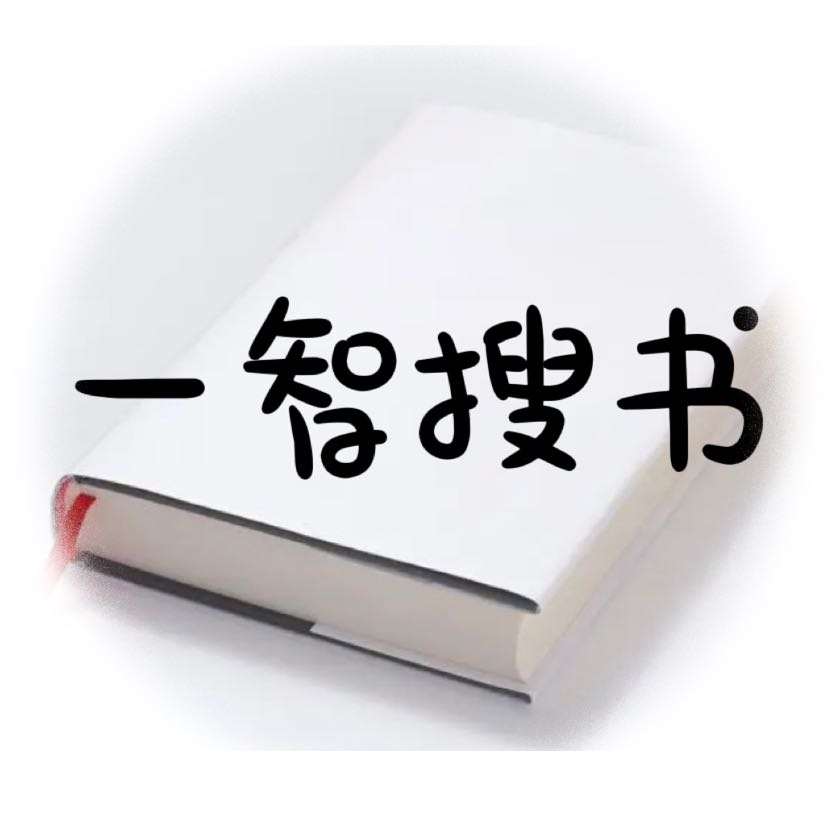#闲话闲章# 转载:【访谈】张广达:我将尽力表彰中华文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广达文集三卷:《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这是一套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著作。不慕荣利的张广达先生渐为两岸学术界理解。
父亲教会他与世无争
张广达家学渊源。张广达介绍,父亲张锡彤是燕京大学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资历而升教授者。“他对我的培育,使我较早知道怎么写论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我还很小,他经常带我进王府大街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即今位于社科院考古所院内的社科院图书馆的前身);我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有一种为人要懂得谦逊的家教。再有,父亲要我刻苦,但从来不主张我争什么,所以我渐次学会了与世无争。”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教诲,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1952年,大陆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至西郊,以燕园为校区。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谈起在大陆的故交,张广达兴味盎然。张广达的夫人徐庭云就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任教中央民族大学,他们家和王钟翰同住一楼。而张广达1978年在北大历史系恢复教职后,得与王永兴先生在学术上交往。我谈起两位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都有师承关系,但与陈先生这一代学者相比,不免浪费了许多光阴在运动里,殊为可惜。张广达说:“是很可惜,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念书人的共同感觉,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不是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我们议论这一情况,也感佩许多知识人在多灾多难之中还是埋头学术研究。张广达说:“中国的文明能够一贯延续下来,这是值得研究的,与很多的古代文明国家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像希腊文明等都断了,而中国历代总有一些人起着脊梁骨的作用。”
二十余年来,张广达奔波于海外,靠在多地教学为生,但常住地是巴黎。张广达任教美国费城宾州大学(UPenn)期间,匹茨堡大学的许倬云先生到访该校。其后,张广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三年,其间和余英时先生在学术上有了交往。
金庸读博士不容易
我提起金庸正在随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张广达曾就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作过简单评述,于是我寄过一套“张广达文集”给金庸。张广达笑道:“金庸的小说,我一本也没看过。我去剑桥的时候见过麦大维,在那篇书评中,我只是觉得唐代还有在律令体制的基层工作的士大夫,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金庸这么大年纪还去读博士,不容易。”
我问:“在西方世界生活了这么久,如何看待所谓的‘国学’?”张广达说:“我觉得国学在知识论和科学认知方面有所欠缺,但有助于培育人的精神境界,西方往往由于个人的一些烦恼就得找心理医生求得辅导。此外,中国的学者自孔孟老庄以下,不管是老庄提倡个人解脱,还是孔孟要入世,都从不同角度要求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是中国学问独到之处。这也是我觉得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学问的台湾比别处好的地方。至于我个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王阳明的《瘗旅文》曾在我跌倒后召唤我重新上路。”
我说:“听黄进兴先生说,你非常关心台湾的时局,每天晚上都看台湾新闻。”张广达说:“现在台湾表面看很乱,但是它的民主体制初步建立了起来,两党交替也粗具规模。只要我有工夫,睡觉之前都看一眼名嘴们的讨论,因为一个念历史的人还是要关怀现实,研究过去是为了关怀未来。”
名家访谈:“不能简单袭取大唐时代的辉煌”
访问前几次电话联系,我在电话里特别说明等我到了台湾大学校门时,再请他骑单车过来见面。张先生还是早早就在台大门口等候了。我们沿着台大校园的椰林大道边走边聊,初次见面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北大”的土与“燕京”的洋
时代周报:1949年考大学时,你怎么去读物理系呢?
张广达:那个时候凡是念书好的学生,都要报考理工,你要是第一志愿就去念文科,表示你理科不行。那时候就是年轻不输这口气,表明我也是可以念理工的。我学数学、物理理论不成问题,但是我动手操作能力有问题,我的物理实验的误差往往在两位数以上,一次实验不及格可以, ...展开全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广达文集三卷:《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这是一套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著作。不慕荣利的张广达先生渐为两岸学术界理解。
父亲教会他与世无争
张广达家学渊源。张广达介绍,父亲张锡彤是燕京大学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资历而升教授者。“他对我的培育,使我较早知道怎么写论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我还很小,他经常带我进王府大街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即今位于社科院考古所院内的社科院图书馆的前身);我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有一种为人要懂得谦逊的家教。再有,父亲要我刻苦,但从来不主张我争什么,所以我渐次学会了与世无争。”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教诲,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1952年,大陆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至西郊,以燕园为校区。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谈起在大陆的故交,张广达兴味盎然。张广达的夫人徐庭云就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任教中央民族大学,他们家和王钟翰同住一楼。而张广达1978年在北大历史系恢复教职后,得与王永兴先生在学术上交往。我谈起两位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都有师承关系,但与陈先生这一代学者相比,不免浪费了许多光阴在运动里,殊为可惜。张广达说:“是很可惜,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念书人的共同感觉,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不是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我们议论这一情况,也感佩许多知识人在多灾多难之中还是埋头学术研究。张广达说:“中国的文明能够一贯延续下来,这是值得研究的,与很多的古代文明国家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像希腊文明等都断了,而中国历代总有一些人起着脊梁骨的作用。”
二十余年来,张广达奔波于海外,靠在多地教学为生,但常住地是巴黎。张广达任教美国费城宾州大学(UPenn)期间,匹茨堡大学的许倬云先生到访该校。其后,张广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三年,其间和余英时先生在学术上有了交往。
金庸读博士不容易
我提起金庸正在随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张广达曾就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作过简单评述,于是我寄过一套“张广达文集”给金庸。张广达笑道:“金庸的小说,我一本也没看过。我去剑桥的时候见过麦大维,在那篇书评中,我只是觉得唐代还有在律令体制的基层工作的士大夫,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金庸这么大年纪还去读博士,不容易。”
我问:“在西方世界生活了这么久,如何看待所谓的‘国学’?”张广达说:“我觉得国学在知识论和科学认知方面有所欠缺,但有助于培育人的精神境界,西方往往由于个人的一些烦恼就得找心理医生求得辅导。此外,中国的学者自孔孟老庄以下,不管是老庄提倡个人解脱,还是孔孟要入世,都从不同角度要求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是中国学问独到之处。这也是我觉得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学问的台湾比别处好的地方。至于我个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王阳明的《瘗旅文》曾在我跌倒后召唤我重新上路。”
我说:“听黄进兴先生说,你非常关心台湾的时局,每天晚上都看台湾新闻。”张广达说:“现在台湾表面看很乱,但是它的民主体制初步建立了起来,两党交替也粗具规模。只要我有工夫,睡觉之前都看一眼名嘴们的讨论,因为一个念历史的人还是要关怀现实,研究过去是为了关怀未来。”
名家访谈:“不能简单袭取大唐时代的辉煌”
访问前几次电话联系,我在电话里特别说明等我到了台湾大学校门时,再请他骑单车过来见面。张先生还是早早就在台大门口等候了。我们沿着台大校园的椰林大道边走边聊,初次见面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北大”的土与“燕京”的洋
时代周报:1949年考大学时,你怎么去读物理系呢?
张广达:那个时候凡是念书好的学生,都要报考理工,你要是第一志愿就去念文科,表示你理科不行。那时候就是年轻不输这口气,表明我也是可以念理工的。我学数学、物理理论不成问题,但是我动手操作能力有问题,我的物理实验的误差往往在两位数以上,一次实验不及格可以,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