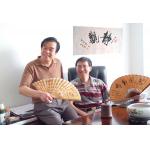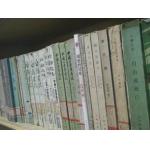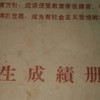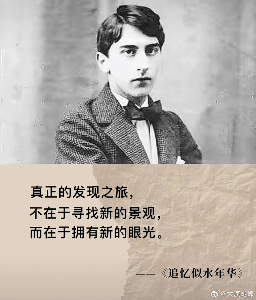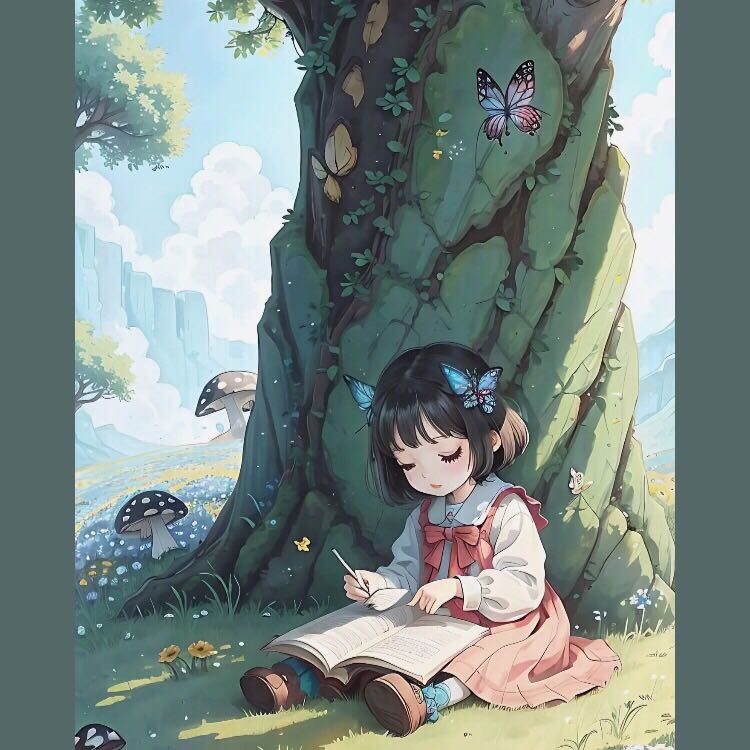#返乡途中的感怀# 忆小时候过元宵节
蛇年元宵节明月高悬,路边正在放烟花的人们,被无处不在的各类“帽子”们制止而悻悻收摊离开。睹此景,小时候过正月十五的那些事又慢慢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元宵节,在山东胶东半岛我们老家叫正月十五,白天,村里有踩高跷、扭秧歌,这种民俗味道浓厚的文化娱乐活动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八。吃罢中午饭稍事休息,母亲会把初二晚上收起来的祭祀供奉、蜡烛等再次一一摆放到位,如果家里挂有“族子”的也要再次放下来,虔诚和仪式感与过年不分二致。
一、放花儿
放烟花在我们老家叫“放花儿”。小时候,烟花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样式,也没有“加特林”这么洋味的名字,最常见的是用棉纸卷着黑火药的一种叫“抖搂机”的男女老少都能放的烟花。
“抖搂机”一般一扎10个,都是手工卷成的,包装最早是灰棉纸,后来也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花纸。前头用浆糊搅拌木渣后封住,中间装有10厘米左右的黑火药,后面还有一段没有火药压扁了的纸筒,防止烧到手。因为这种烟花价格便宜,又安全,最关键是耐放,所以这是当时村里一般家庭给孩子们准备的常见物品。
十五晚上无论走到那里,小伙伴们手里都拿着“刺啦、剌啦”闪着菊黄色亮光的“抖搂机”。放了一会新鲜劲过去了,手里还有一大把,我们会用唾沫把他们粘在墙上贴成一排,然后逐一引燃,霎那间“刺啦、剌啦”声中,照亮了漆黑的夜晚和我们那灿烂的笑脸。
条件稍微好一点人家的孩子,十五晚上还会放上几个“二踢脚”、“钻天猴”等比“抖搂机”更贵些的烟花。后来,集市上出现了一种叫着“魔术弹”的长杆子,一般是10个响的,看着同伴们侧脸手举这种颇具现代气息的烟花,让我羡慕的不得了。
那时候,我们村正月十五晚上大人们会放一种家乡话叫“米锅子”的、类似大爆仗的手工制作的烟花。因为燃放出的火焰很高,喷射面积大,为了安全一般都会在大路等宽阔的地方放。点燃后的“米锅子”喷发出雪花状剌眼亮光,真有一种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感觉。“米锅子”的价格远比“抖搂机”贵的多,所以一个正月十五,村里仅有屈指可数的人家会放上几个,但引来围观的村民却是里三层外三层。
还记得邻居同伴的父亲在高中当化学老师,有一年他放的是上学做实验用的金属镁条,那亮度瞬间秒杀了我手里的“抖搂机”,看着同伴得意的样子,我一下子失去了再放“抖搂机”的兴趣。
二、吃元宵
说实话在上高中以前,我没有吃过元宵,也不知道元宵长什么样,但还记得第一次吃元宵是在邻居家吃的。估计是因为我们那里不产大米的缘故,小时候就没听说过有卖这东西的,所以邻居家收到亲戚带去的元宵后,专门把我们姐弟俩叫去一起吃元宵,现在我已经回味不起第一次吃元宵后的味道了,但这个事一直留在记忆里。
正月十五晚上,母亲会让我先放一挂鞭应应景,这天晚上饺子才是我们过节永恒的硬菜。估计那时候北方绝大多数农村这一天都是吃饺子,吃了半个正月的好饭,这碗饺子的诱惑远远赶不上大年三十那顿。
三、赏花灯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只看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花灯。那时我大概也就7-8岁,村里一个有文化的老人在正月十五晚上提着一个用玉米和高梁秸等扎成类似宫灯的花灯,从那后再也没有见过。
上世纪7-80年代农村没有现在各式各样的塑料花灯,虽然没有这些时兴货,但我们也有我们的“灯”。这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豆面灯。
正月十五下午,母亲准备好一切物品后,会按照我的属相做一盏兔子造型的豆面灯。做成型的豆面灯先要上锅蒸一下,然后用棉线绳做成灯捻儿,兔子背上的灯碗里倒上花生油,再用一根绳子将其固定住,系在一根小木棍上,豆面灯就算做成了。
十五晚上,母亲会让我提着豆面灯把家里每个房间、院里每个角落都照一遍,寓意一年里亮亮堂堂、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因为豆面在那时候是紧缺商品,我们家其它地方的灯只能用蜡烛来替代。除了屋内各处外,屋外的窗台上、大门墩上、猪圈、厢房门前都要点上,但冬天风大,这些“灯”一会就被吹灭了,母亲会赶快再次点上。
提着玩了一晚上的豆面灯,被油浸入面又加上火的烘烤,这时的豆面发出淡淡的清香。虽然我很舍不得,但第2天母亲仍然会趁着没有变质将其蒸熟后切成片晾干保存,做菜的时候放入一些,吃着这难得的风味我又忘记了难舍的豆面灯。
母亲常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眼看再过两天正月十七就要开学了,这时才发现寒假作业还没有写完,于是半正月的快乐劲,一下子全没了。
(前2张图片来之网络)
蛇年元宵节明月高悬,路边正在放烟花的人们,被无处不在的各类“帽子”们制止而悻悻收摊离开。睹此景,小时候过正月十五的那些事又慢慢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元宵节,在山东胶东半岛我们老家叫正月十五,白天,村里有踩高跷、扭秧歌,这种民俗味道浓厚的文化娱乐活动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八。吃罢中午饭稍事休息,母亲会把初二晚上收起来的祭祀供奉、蜡烛等再次一一摆放到位,如果家里挂有“族子”的也要再次放下来,虔诚和仪式感与过年不分二致。
一、放花儿
放烟花在我们老家叫“放花儿”。小时候,烟花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样式,也没有“加特林”这么洋味的名字,最常见的是用棉纸卷着黑火药的一种叫“抖搂机”的男女老少都能放的烟花。
“抖搂机”一般一扎10个,都是手工卷成的,包装最早是灰棉纸,后来也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花纸。前头用浆糊搅拌木渣后封住,中间装有10厘米左右的黑火药,后面还有一段没有火药压扁了的纸筒,防止烧到手。因为这种烟花价格便宜,又安全,最关键是耐放,所以这是当时村里一般家庭给孩子们准备的常见物品。
十五晚上无论走到那里,小伙伴们手里都拿着“刺啦、剌啦”闪着菊黄色亮光的“抖搂机”。放了一会新鲜劲过去了,手里还有一大把,我们会用唾沫把他们粘在墙上贴成一排,然后逐一引燃,霎那间“刺啦、剌啦”声中,照亮了漆黑的夜晚和我们那灿烂的笑脸。
条件稍微好一点人家的孩子,十五晚上还会放上几个“二踢脚”、“钻天猴”等比“抖搂机”更贵些的烟花。后来,集市上出现了一种叫着“魔术弹”的长杆子,一般是10个响的,看着同伴们侧脸手举这种颇具现代气息的烟花,让我羡慕的不得了。
那时候,我们村正月十五晚上大人们会放一种家乡话叫“米锅子”的、类似大爆仗的手工制作的烟花。因为燃放出的火焰很高,喷射面积大,为了安全一般都会在大路等宽阔的地方放。点燃后的“米锅子”喷发出雪花状剌眼亮光,真有一种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感觉。“米锅子”的价格远比“抖搂机”贵的多,所以一个正月十五,村里仅有屈指可数的人家会放上几个,但引来围观的村民却是里三层外三层。
还记得邻居同伴的父亲在高中当化学老师,有一年他放的是上学做实验用的金属镁条,那亮度瞬间秒杀了我手里的“抖搂机”,看着同伴得意的样子,我一下子失去了再放“抖搂机”的兴趣。
二、吃元宵
说实话在上高中以前,我没有吃过元宵,也不知道元宵长什么样,但还记得第一次吃元宵是在邻居家吃的。估计是因为我们那里不产大米的缘故,小时候就没听说过有卖这东西的,所以邻居家收到亲戚带去的元宵后,专门把我们姐弟俩叫去一起吃元宵,现在我已经回味不起第一次吃元宵后的味道了,但这个事一直留在记忆里。
正月十五晚上,母亲会让我先放一挂鞭应应景,这天晚上饺子才是我们过节永恒的硬菜。估计那时候北方绝大多数农村这一天都是吃饺子,吃了半个正月的好饭,这碗饺子的诱惑远远赶不上大年三十那顿。
三、赏花灯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只看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花灯。那时我大概也就7-8岁,村里一个有文化的老人在正月十五晚上提着一个用玉米和高梁秸等扎成类似宫灯的花灯,从那后再也没有见过。
上世纪7-80年代农村没有现在各式各样的塑料花灯,虽然没有这些时兴货,但我们也有我们的“灯”。这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豆面灯。
正月十五下午,母亲准备好一切物品后,会按照我的属相做一盏兔子造型的豆面灯。做成型的豆面灯先要上锅蒸一下,然后用棉线绳做成灯捻儿,兔子背上的灯碗里倒上花生油,再用一根绳子将其固定住,系在一根小木棍上,豆面灯就算做成了。
十五晚上,母亲会让我提着豆面灯把家里每个房间、院里每个角落都照一遍,寓意一年里亮亮堂堂、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因为豆面在那时候是紧缺商品,我们家其它地方的灯只能用蜡烛来替代。除了屋内各处外,屋外的窗台上、大门墩上、猪圈、厢房门前都要点上,但冬天风大,这些“灯”一会就被吹灭了,母亲会赶快再次点上。
提着玩了一晚上的豆面灯,被油浸入面又加上火的烘烤,这时的豆面发出淡淡的清香。虽然我很舍不得,但第2天母亲仍然会趁着没有变质将其蒸熟后切成片晾干保存,做菜的时候放入一些,吃着这难得的风味我又忘记了难舍的豆面灯。
母亲常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眼看再过两天正月十七就要开学了,这时才发现寒假作业还没有写完,于是半正月的快乐劲,一下子全没了。
(前2张图片来之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