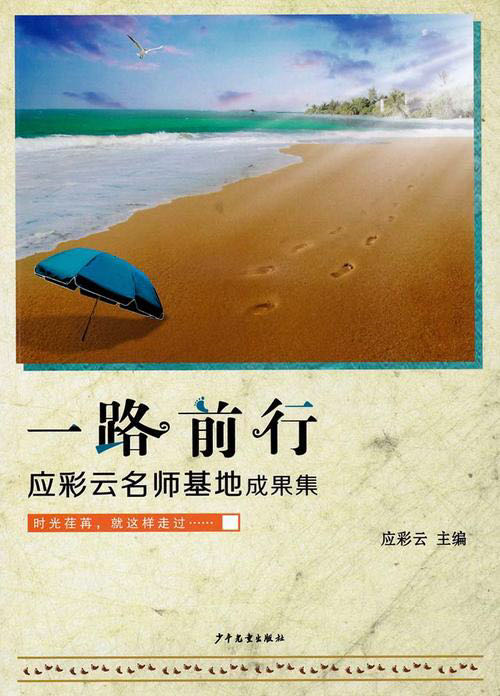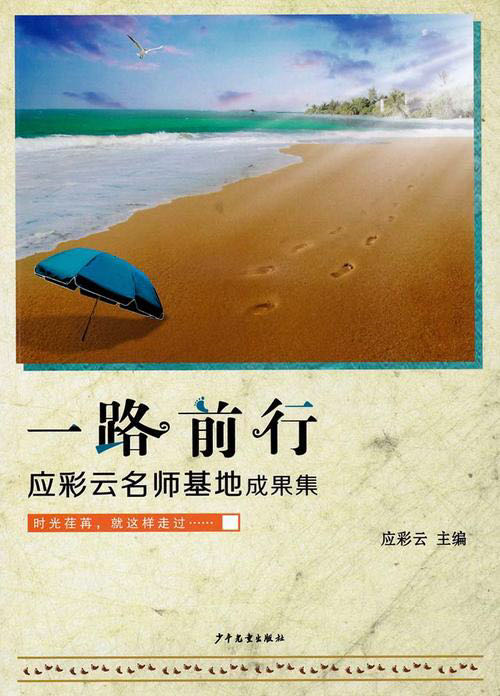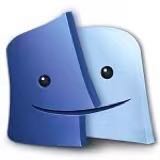《受活》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是关于人类幸福生活到底在哪儿的一部书。可那时候围绕着《受活》起涌的纷争,如旷野间的风霜雨雪,初春时的光和月明。说好的,到了天上;不好的,到了脚下,关于现实和现实主义,关于我们的社会和乌托邦生存,关于现代和后现代,关于狂想和寓言,关于魔幻和想象,关于方言和结构,关于黑色幽默和历史疼痛,关于文学和阎连科的写作;究竟该是何样一个合适的评说,如此等等。这些话意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一部小说写完之后,作者对小说的注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二是文学与社会,这个话题是恒久不衰的。
——阎连科《念求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