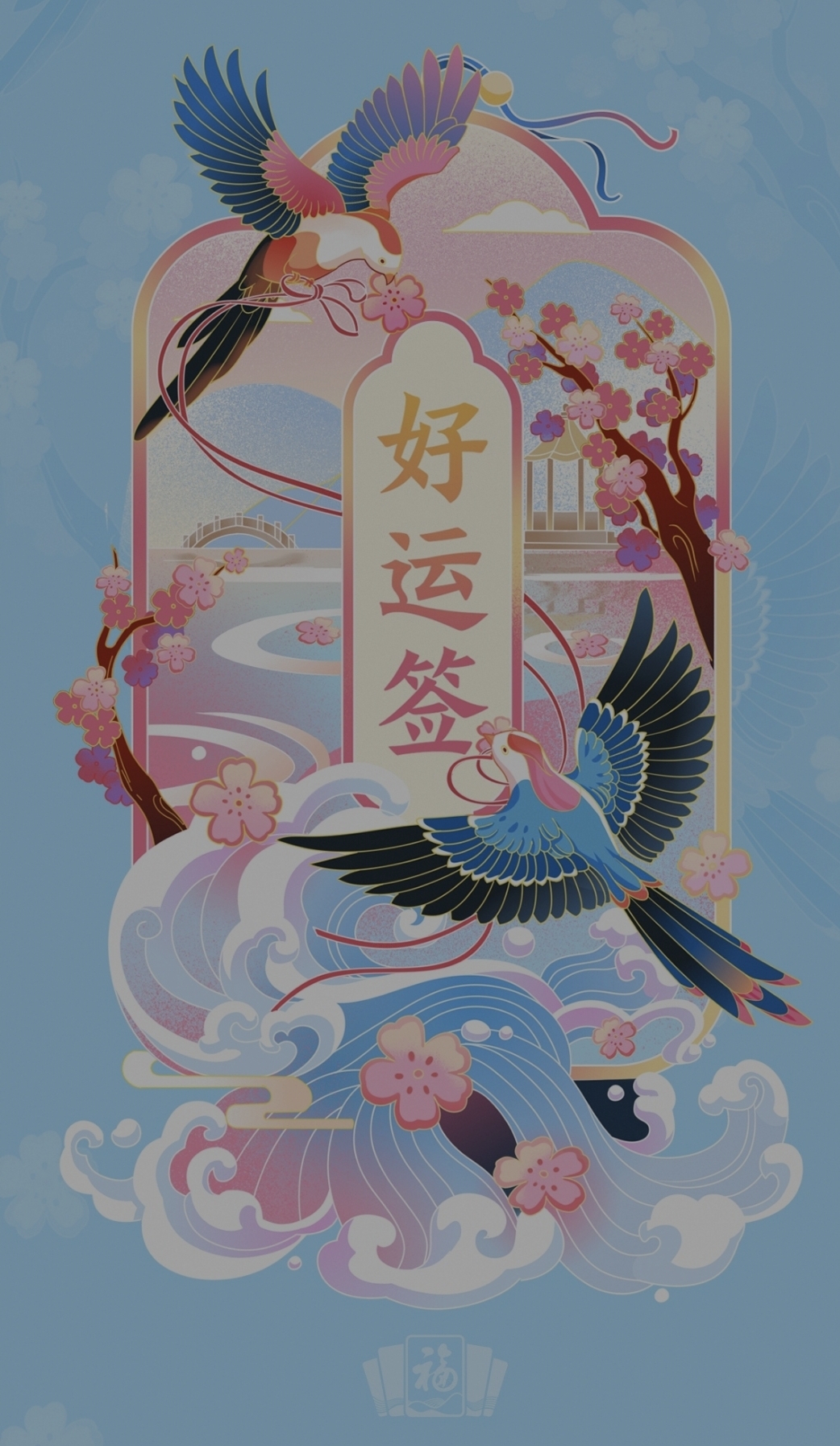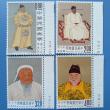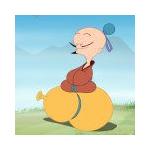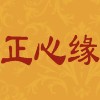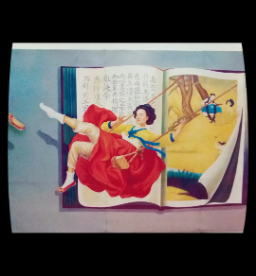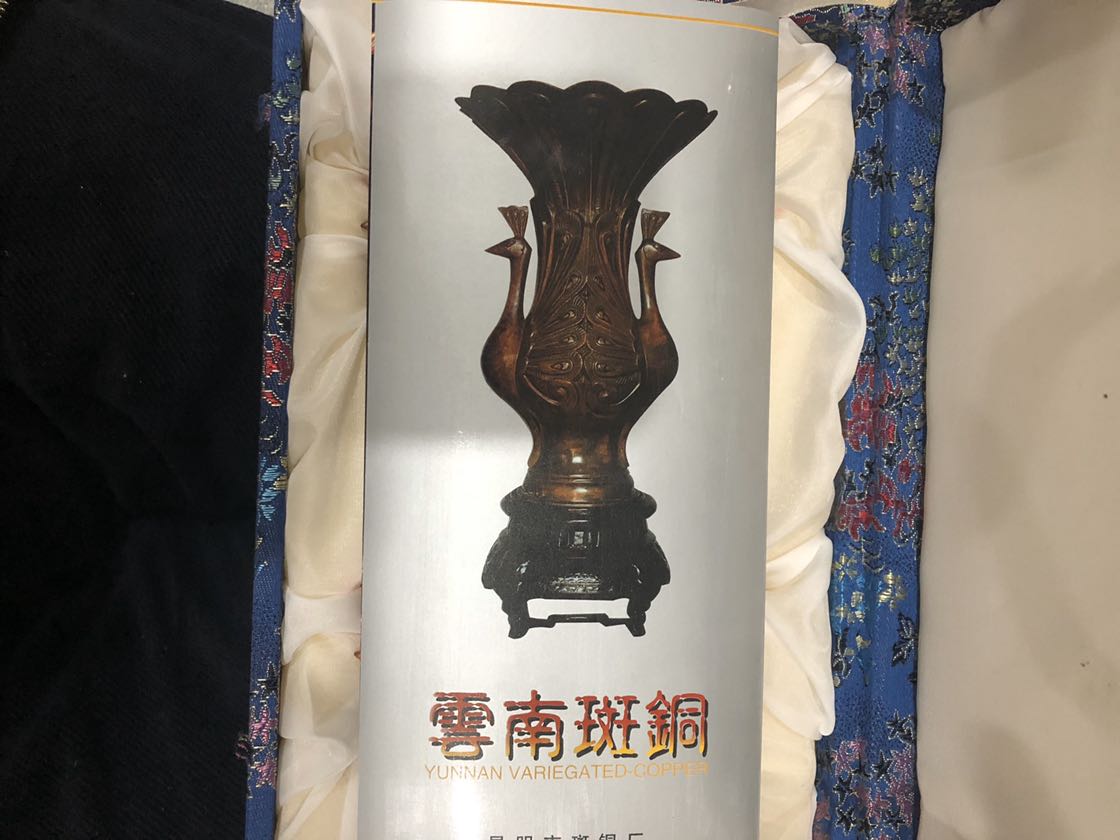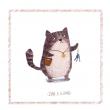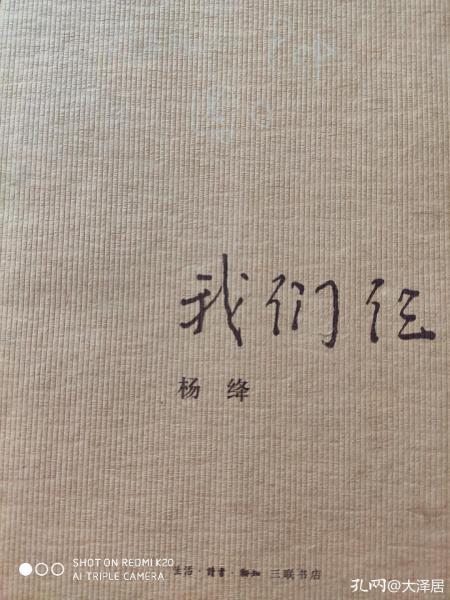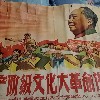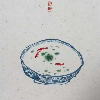“美国有一百来个参议员,而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
这是1981年,邓小平在国宴上,被问及“为何将陈香梅安排在第一贵宾席”时给出的回答。
被誉为“全世界只有一个”的陈香梅的确不是凡人,她的传奇一生诠释了一等女人的活法:长得漂亮,活得清醒。

陈香梅
陈香梅生于1925年,祖籍是广东佛山,出生地却是北京。因为身逢乱世,年仅12岁那年,她就因日本侵华不得已和全家一起流亡香港。
陈香梅一家刚到香港没几年,香港沦陷。由于过度操劳致病,她的母亲在这年离开了人世,此时,她年仅16岁。
母亲死后,陈香梅和五个姐妹陷入了无尽的迷茫:父亲远在美国,她们身边已经没有依靠了。没有依靠,就靠自己。陈香梅和五姐妹咬着牙,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
流亡路上有多苦,流亡百姓有多可怜,陈香梅就有多恨日本人。但怨恨不是力量,因怨恨而起的奋斗才有力量。陈香梅更加发奋地读书了,她确信:只有他们站起来,国家才有复兴的可能。
连续几年的流亡,在锻炼了陈香梅处事能力的同时,也让她有了超越同龄人的坚韧。
1944年,19岁的陈香梅怀着理想加入了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她是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记者。因为陈香梅英语流利,她工作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采访时任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陈纳德。
对于刚刚成为记者的陈香梅而言,陈纳德是真正的大人物。为了这次采访能顺利进行,她做了很多准备。她事先已了解到:因“飞虎队” 驾驶着美制战斗机,屡战屡捷,中国老百姓非常尊敬、支持他们。
她还打探到:“飞虎队”统帅陈纳德很不喜欢记者,他经常让他们下不来台。在新闻界,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存在,他更像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背地里,记者们都管他叫“老头子”。
记者同行越是对陈纳德“嗤之以鼻”,陈香梅就越想尽快接触这个“老头”。她和普通记者不一样,普通记者都倾向于选择容易的事做,而她却喜欢做那些难度更大的事。如果一件事非得她跳起来才够得着,她会更加有动力。
陈纳德,恰恰是她跳起来,才够得着的存在。
采访陈纳德那天,陈香梅特地穿了一身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她将乌黑的秀发编成了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垂在胸前。这身打扮配上她俊秀、有东方美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格外与众不同。
那天,推开陈纳德将军办公室的大门后,陈香梅就见到了身着一身笔挺军装站在窗前的陈纳德,只一眼,她就被他那双放着光亮的眼睛吸引住了。
陈香梅在门口下意识地停留了一下,就在她发愣的当口,起先还一脸严肃的陈纳德竟径直走了过来,并握住她的手道用温和的语气道:“上午好,女士,我是克莱尔·李·陈纳德。”
这样的陈纳德与她之前通过别人之口了解的“陈纳德”,太不一样了,陈香梅愣了下才恍若从梦中惊醒地握住他的手回到:“将军好,我叫陈香梅。”
陈香梅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这似乎是疏漏,按理,她应该说“我是中央社记者陈香梅”。这个疏漏,让她后来一直纳闷不已。“或许,这是命中注定吧!”她只能如此解释。
陈香梅初印象中的陈纳德给了她“春风拂面”的感觉,她透过那张脸,读懂了常人看不到的他,她后来写道:
“他的脸孔遍布深刻的皱纹,有着一个倔强的下颚,看起来强韧而果决,一堆深沉的棕色眸子里流露出坚忍的神色。我对他的瞬间印象是: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力量和勇气,兼有高超的智慧。”

陈纳德与陈香梅(右)在云南
人都说“一个心里有什么,才能看见什么”,能透过第一眼,看到陈纳德的“意志、力量、勇气、智慧”的陈香梅,本已不是普通女子。她和他是相似的,所以,当他们真的坐下来聊天时,两人竟都有了相见恨晚之感。
陈香梅发现自己和陈纳德有太多相似处:他们都出身望族,却早早失去了母亲的照拂,他们都还深爱着对方的家乡。
陈纳德在惊讶之余,也对这个女记者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确信:他和她这样的遇见,是世间难得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可遇不可求”。
那次采访后,两人道别时,陈香梅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陈纳德,她竟在这位年已50岁的将军的眼里,看到了孩子般的不舍。她在感动之余,也不由得心里一动。
有了第一次成功采访的经验后,后面的采访就容易多了。陈香梅开始频繁出入第14航空司令部。
陈香梅通过采访了解了陈纳德的身世和战绩,她用一个个故事将他的一生报道出来了。显然,陈纳德自己也很满意她的报道。
越是了解陈纳德,陈香梅越是对这个饱经风霜的男人有好感。从小缺乏父爱的她,甚至在和他的交往中,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直到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是她的父亲从未给过她的。他的父亲长期未与她们母女生活在一块,他和母亲之间也并没有真正的爱情,重男轻女的他,也极少给过她们关爱。母亲刚去世不久,他就给自己找了续弦。
陈香梅多少有些恨父亲,她在替母亲不值的同时,也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找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在未遇见陈纳德前,她并不知道“顶 ...展开全文
这是1981年,邓小平在国宴上,被问及“为何将陈香梅安排在第一贵宾席”时给出的回答。
被誉为“全世界只有一个”的陈香梅的确不是凡人,她的传奇一生诠释了一等女人的活法:长得漂亮,活得清醒。

陈香梅
陈香梅生于1925年,祖籍是广东佛山,出生地却是北京。因为身逢乱世,年仅12岁那年,她就因日本侵华不得已和全家一起流亡香港。
陈香梅一家刚到香港没几年,香港沦陷。由于过度操劳致病,她的母亲在这年离开了人世,此时,她年仅16岁。
母亲死后,陈香梅和五个姐妹陷入了无尽的迷茫:父亲远在美国,她们身边已经没有依靠了。没有依靠,就靠自己。陈香梅和五姐妹咬着牙,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
流亡路上有多苦,流亡百姓有多可怜,陈香梅就有多恨日本人。但怨恨不是力量,因怨恨而起的奋斗才有力量。陈香梅更加发奋地读书了,她确信:只有他们站起来,国家才有复兴的可能。
连续几年的流亡,在锻炼了陈香梅处事能力的同时,也让她有了超越同龄人的坚韧。
1944年,19岁的陈香梅怀着理想加入了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她是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记者。因为陈香梅英语流利,她工作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采访时任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陈纳德。
对于刚刚成为记者的陈香梅而言,陈纳德是真正的大人物。为了这次采访能顺利进行,她做了很多准备。她事先已了解到:因“飞虎队” 驾驶着美制战斗机,屡战屡捷,中国老百姓非常尊敬、支持他们。
她还打探到:“飞虎队”统帅陈纳德很不喜欢记者,他经常让他们下不来台。在新闻界,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存在,他更像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背地里,记者们都管他叫“老头子”。
记者同行越是对陈纳德“嗤之以鼻”,陈香梅就越想尽快接触这个“老头”。她和普通记者不一样,普通记者都倾向于选择容易的事做,而她却喜欢做那些难度更大的事。如果一件事非得她跳起来才够得着,她会更加有动力。
陈纳德,恰恰是她跳起来,才够得着的存在。
采访陈纳德那天,陈香梅特地穿了一身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她将乌黑的秀发编成了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垂在胸前。这身打扮配上她俊秀、有东方美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格外与众不同。
那天,推开陈纳德将军办公室的大门后,陈香梅就见到了身着一身笔挺军装站在窗前的陈纳德,只一眼,她就被他那双放着光亮的眼睛吸引住了。
陈香梅在门口下意识地停留了一下,就在她发愣的当口,起先还一脸严肃的陈纳德竟径直走了过来,并握住她的手道用温和的语气道:“上午好,女士,我是克莱尔·李·陈纳德。”
这样的陈纳德与她之前通过别人之口了解的“陈纳德”,太不一样了,陈香梅愣了下才恍若从梦中惊醒地握住他的手回到:“将军好,我叫陈香梅。”
陈香梅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这似乎是疏漏,按理,她应该说“我是中央社记者陈香梅”。这个疏漏,让她后来一直纳闷不已。“或许,这是命中注定吧!”她只能如此解释。
陈香梅初印象中的陈纳德给了她“春风拂面”的感觉,她透过那张脸,读懂了常人看不到的他,她后来写道:
“他的脸孔遍布深刻的皱纹,有着一个倔强的下颚,看起来强韧而果决,一堆深沉的棕色眸子里流露出坚忍的神色。我对他的瞬间印象是: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力量和勇气,兼有高超的智慧。”

陈纳德与陈香梅(右)在云南
人都说“一个心里有什么,才能看见什么”,能透过第一眼,看到陈纳德的“意志、力量、勇气、智慧”的陈香梅,本已不是普通女子。她和他是相似的,所以,当他们真的坐下来聊天时,两人竟都有了相见恨晚之感。
陈香梅发现自己和陈纳德有太多相似处:他们都出身望族,却早早失去了母亲的照拂,他们都还深爱着对方的家乡。
陈纳德在惊讶之余,也对这个女记者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确信:他和她这样的遇见,是世间难得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可遇不可求”。
那次采访后,两人道别时,陈香梅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陈纳德,她竟在这位年已50岁的将军的眼里,看到了孩子般的不舍。她在感动之余,也不由得心里一动。
有了第一次成功采访的经验后,后面的采访就容易多了。陈香梅开始频繁出入第14航空司令部。
陈香梅通过采访了解了陈纳德的身世和战绩,她用一个个故事将他的一生报道出来了。显然,陈纳德自己也很满意她的报道。
越是了解陈纳德,陈香梅越是对这个饱经风霜的男人有好感。从小缺乏父爱的她,甚至在和他的交往中,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直到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是她的父亲从未给过她的。他的父亲长期未与她们母女生活在一块,他和母亲之间也并没有真正的爱情,重男轻女的他,也极少给过她们关爱。母亲刚去世不久,他就给自己找了续弦。
陈香梅多少有些恨父亲,她在替母亲不值的同时,也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找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在未遇见陈纳德前,她并不知道“顶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