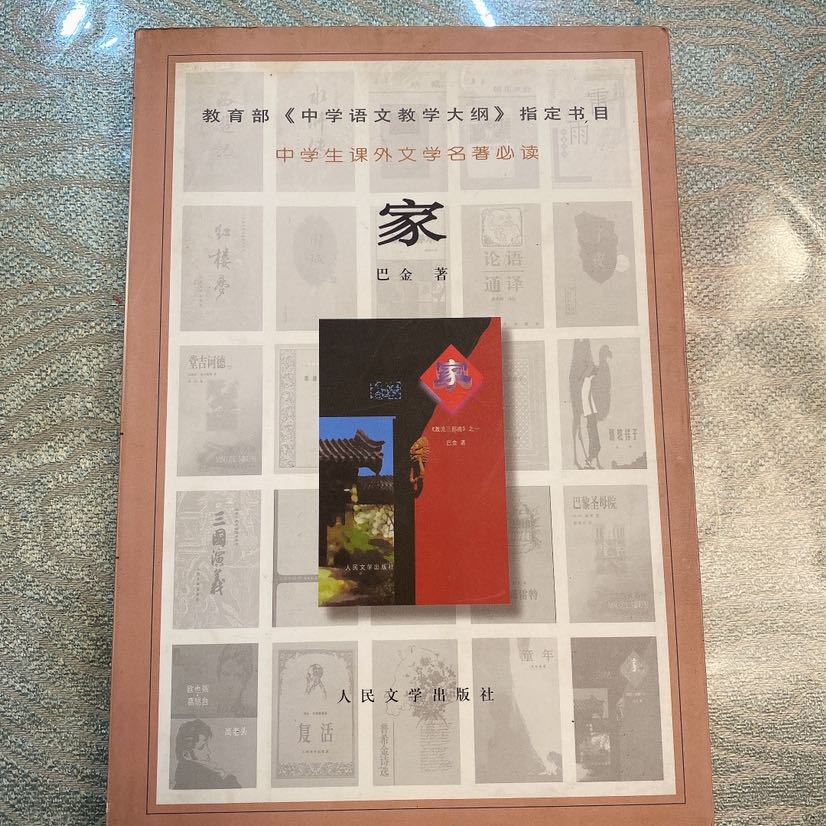二十年前我在纽约
这些天阿富汗每天都占据头条和头几条新闻,让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年前的往事,我竟然在纽约为了普及阿富汗与中国交界的小知识跟几个西方人闹的不愉快。看护照我是二十年前的今天买了一张700$的返程机票到的纽约!麻鸭,20年!我的文学地图上从而有了纽约。
当然那种争吵首先是因为他们压根认为我在瞎编引起的,西方的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关心中亚和中国,你说点什么他们基本不信,甚至认为你是编造。对他们不能恼,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
9.11之前的大半个月我们一直在纽约乡下的一个国际写作坊当访问作家,不舍昼夜地记录着自己的幻想。忽然在一个上午那个西班牙作家四处呼叫说世贸大楼被飞机撞着火了,招呼大家去看电视直播。这些来自各国的作家们看着飞机撞向大楼和大楼轰然坍塌的直播,瞠目结舌-一切都比他们虚构的作品令人胆寒。大家长时间里重复的一个词就是devastated,神经崩溃。
美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了!
我们都写不下去了,几乎整天聚在电视机前木然地看电视直播,换着台看。看了两天才开始议论点什么,但大都不着边际。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切身恐怖问题是:这一期写作坊快要到期了,下一批作家要进驻了,我们必须离开腾地方。
其实大家私下盼望的是机场彻底关闭,那样我们就有理由不走,可以安全地躲上一段时间。写作坊的负责人很是体谅民情,告诉我们:下一期的外国作家大都吓破了胆,纷纷推迟来美,反正房子空着,你们就住下去,写作坊照样管吃管住。
可机场不久就正式开放了,我们没有理由不走,唯一不走的理由就是“我害怕”。我们毅然决定如期离开美国,哪怕自己的那架飞机被什么人劫持了自己当了人肉炸弹 - 不敢想,不敢说,嘴上只是坚定地说走!
这个时候的这些访问作家们似乎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想不代表都不行,因为大家在互相询问各国政府和老百姓的态度,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就成了那个国家的发言人,尽管你宣称那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那天饭桌上人们问起我中国的态度,我说中国政府在事件一发生就谴责了恐怖主义,这两天又关闭了中国和阿富汗边界,防止恐怖分子潜逃到中国。
简单的一句话居然引来哄笑,他们不相信中国和阿富汗交界!一个法国诗人对我的无知表示了怜悯,随后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很同情我。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甚至不屑于了解,这是无奈的事。我只能准备饭后拿地图给他们看了。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上网,整个写作坊里也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可拨号上网,很不方便,不能立即调地图看。但就在这时一个德国作家火上浇油地嘲弄说:“中国和德国的边界也要关闭了吧?”
我怒不可遏,立即要爆发。还是那个好心的西班牙作家善解人意,笑着递给我酒瓶子说:“你完全可以拿这个砸他。”大家都笑着说对,砸他。那一刻大家觉得德国作家太过分,对一个地理知识差的人也不至于这么穷追猛打。那德国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堆笑着说:“对不起,我是开玩笑。”
饭后我回宿舍拿来随身带的世界地图,悄声对那个法国诗人说:“嘿,兄弟,我必须纠正你的错误,看看,中国和阿富汗的边界有多么窄,可能才10米吧,可那也是两国边界,照样能过卡车,别说一个拉登了。”那骄傲的法国诗人很尴尬地笑了。一起“公案”就这么了结了。
第二天,那德国作家居然首先跑来告诉我:“我听说了,是他错了,他不懂。”这似乎是在向我表示道歉。以后又有几个人对我说是那个法国诗人错了。他们居然很在意这件事,好像还查对了地图,还在背后议论了,这我没想到。连那个似乎很超然的俄国作家也突然对我说“对不起。”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当初虽然没表态,但心里相信法国诗人是对的,所以对不起我。
随着每个人访问期满,我们依次告别写作坊奔赴纽约肯尼迪机场。每个人的告别都显得沉重无比,因为大家都知道形势叵测,心里都忐忑不安,天知道会不会当了人弹。那几天,每天早晨的告别都很沉重悲凉,大家只有默默拥抱亲吻,只有一句话就是:“到了家来电话。”这是唯一可说的。
我到了伦敦就立即给写作坊打了电话报平安,接电话的恰好是那个法国诗人。这是我们那批人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平安抵达的电话都能给后出来的人增强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逃走”后别人总会望着天念叨:谁谁现在正在大西洋上空,上帝保佑他,其实也是在保佑自己。愿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没有悲惨的9.11事件,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各自关在自己屋子里埋头写作的个体,最多晚餐时闲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而已。因了9.11,我们有了透视各自心理的机会,在惨剧没有伤害到自己时居然还顾得上闹点儿小小的“国际”冲突,以后又有了相互的理解。对同样的历史事件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记忆,大难当头,我在纽约乡下的记忆除了无边的恐惧,竟还有这么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真是意想不到。(见《我的文学地图》)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