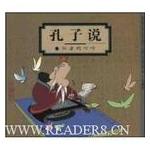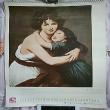#阅读摘录# 一年到头,唯独今天我舒舒服服睡了一个懒觉。
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
睡眠充足花费的奢侈时间,对更新今天的动态已经略显仓促,我只好省力从一本书上摘录几段关于书的文字来充数。
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件事,阅读的最高享受就是意外地发现我们和不认识、住在半个地球之外、甚至可能已死了好几世纪的人,心有戚戚焉矣!而他们已设法描写出我们确切的感觉,想到我们确切的意念。只是,他们比我们做得要好,别具风格而更流利,更有智慧更聪明。光是和"我们的分身"、"我们的兄弟"的这种偶然相逢﹣﹣借用波德莱尔所用的公式﹣﹣就值得我们去尝试我们从未听过、在学校从未教过的作家了。
在法国小说家丹尼尔·贝纳的非小说书《有如小说》里,他提供了一张"读者的权利"。上面载有下列十项权利:
1、不读的权利。
2、跳页的权利。
3、不读完的权利。
4、重读的权利。
5、读任何东西的权利。
6、消遣的权利。
7、随处读的权利。
8、浏览的权利。
9、大声读出来的权利。
10、不必为自己的品位辩护的权利。
总而言之,对爱书者来说,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是个悲哀的时代。更悲哀的是,你得和你心爱的藏书分手。你不得不羡慕德尼.狄德罗。他由于"[他的]财务无足可观"而被迫要把他的藏书卖掉,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天底下最慷慨的买家。俄国的卡捷琳娜二世不只让他在他有生之年保管她的新购之书,且由于他"费心看管",自此奖励他一笔为数可观的年俸。
然后就是塞缪尔·佩皮斯,英国的日记作家。他对他的书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在遗嘱中为此立下条款,规定这批书必须"整体保持,不可分割,不可买卖,不可以任何方式删减、破坏或挪用。"因而,这批藏书在他死后三百多年,还能够完整无缺,甚至以他偏好的次序排列,放在特别照他指示订制的书箱里,储藏在剑桥的抹大拉学院。
他爱书,书的感觉,书摆出来的样子……镇上又脏又旧的书店是他最喜欢的寻宝之地,而他一生都认真地查询出版商印的目录,找他可能有兴趣的书籍。他在其他方面很节俭,常常到了吝啬的地步,但只要与书有关,他就立刻变得奢侈起来,一点不觉得内疚……但他绝不是个"收藏家";引起他贪婪的不是稀有的古书或精美的装订,最主要的,是书壳之间的内容。他不只爱书、买书﹣﹣他还读书。
这就是恩斯特·鲍尔为卡夫卡所作的传记中一段。
他毫无目标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悲惨的景象,他的
坏腿、他的破衣都益发凸显他那疲倦而脆弱的形象。
"这就是我一直留在这所房子里的原因,"他继续说道,"我失去的书的鬼魂就在这四面墙里。"
我在筛选我的书,决定什么该留下,什么该去掉。
我不时停下来,摇摇头。到底是什么促使我去买这么多书的?是疯了吗?或只不过是贪婪?
我偶尔也被自己的天真所感动。还是我该说"野心"?我真的相信自己会读完所有这些书﹣﹣而因此变成更好的人吗?
我在这样检阅我的图书馆,把良莠分开。这件工作变得愈来愈难。书,也像在超级市场的货物,有它们上架的寿命。有些的新鲜期不会超过一个季节;有些则可持续几个世纪。麻烦的是那些在两者之间的,那些不会永久持续,但在未来几年还是好的。这些值不值得留下呢?我怎么知道哪种决定才不会后悔呢?
也许,我们在旧书没有读完就不断把新书搬回家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让自己环坐在这些书中,就幻想自己已经解决了自古以来的一个难题,就是以生之有涯追知之无涯。
当然,在现实中,我们所做的就是买一大堆书。
说到这个,最好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书店,尤其是只卖新的精装本的那些书店。这其实是最不该去的地方。我们的第一站永远应该是旧书店。选择可能不那么全面,但我们却可能以便宜得多的价钱找到宝贝。
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
睡眠充足花费的奢侈时间,对更新今天的动态已经略显仓促,我只好省力从一本书上摘录几段关于书的文字来充数。
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件事,阅读的最高享受就是意外地发现我们和不认识、住在半个地球之外、甚至可能已死了好几世纪的人,心有戚戚焉矣!而他们已设法描写出我们确切的感觉,想到我们确切的意念。只是,他们比我们做得要好,别具风格而更流利,更有智慧更聪明。光是和"我们的分身"、"我们的兄弟"的这种偶然相逢﹣﹣借用波德莱尔所用的公式﹣﹣就值得我们去尝试我们从未听过、在学校从未教过的作家了。
在法国小说家丹尼尔·贝纳的非小说书《有如小说》里,他提供了一张"读者的权利"。上面载有下列十项权利:
1、不读的权利。
2、跳页的权利。
3、不读完的权利。
4、重读的权利。
5、读任何东西的权利。
6、消遣的权利。
7、随处读的权利。
8、浏览的权利。
9、大声读出来的权利。
10、不必为自己的品位辩护的权利。
总而言之,对爱书者来说,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是个悲哀的时代。更悲哀的是,你得和你心爱的藏书分手。你不得不羡慕德尼.狄德罗。他由于"[他的]财务无足可观"而被迫要把他的藏书卖掉,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天底下最慷慨的买家。俄国的卡捷琳娜二世不只让他在他有生之年保管她的新购之书,且由于他"费心看管",自此奖励他一笔为数可观的年俸。
然后就是塞缪尔·佩皮斯,英国的日记作家。他对他的书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在遗嘱中为此立下条款,规定这批书必须"整体保持,不可分割,不可买卖,不可以任何方式删减、破坏或挪用。"因而,这批藏书在他死后三百多年,还能够完整无缺,甚至以他偏好的次序排列,放在特别照他指示订制的书箱里,储藏在剑桥的抹大拉学院。
他爱书,书的感觉,书摆出来的样子……镇上又脏又旧的书店是他最喜欢的寻宝之地,而他一生都认真地查询出版商印的目录,找他可能有兴趣的书籍。他在其他方面很节俭,常常到了吝啬的地步,但只要与书有关,他就立刻变得奢侈起来,一点不觉得内疚……但他绝不是个"收藏家";引起他贪婪的不是稀有的古书或精美的装订,最主要的,是书壳之间的内容。他不只爱书、买书﹣﹣他还读书。
这就是恩斯特·鲍尔为卡夫卡所作的传记中一段。
他毫无目标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悲惨的景象,他的
坏腿、他的破衣都益发凸显他那疲倦而脆弱的形象。
"这就是我一直留在这所房子里的原因,"他继续说道,"我失去的书的鬼魂就在这四面墙里。"
我在筛选我的书,决定什么该留下,什么该去掉。
我不时停下来,摇摇头。到底是什么促使我去买这么多书的?是疯了吗?或只不过是贪婪?
我偶尔也被自己的天真所感动。还是我该说"野心"?我真的相信自己会读完所有这些书﹣﹣而因此变成更好的人吗?
我在这样检阅我的图书馆,把良莠分开。这件工作变得愈来愈难。书,也像在超级市场的货物,有它们上架的寿命。有些的新鲜期不会超过一个季节;有些则可持续几个世纪。麻烦的是那些在两者之间的,那些不会永久持续,但在未来几年还是好的。这些值不值得留下呢?我怎么知道哪种决定才不会后悔呢?
也许,我们在旧书没有读完就不断把新书搬回家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让自己环坐在这些书中,就幻想自己已经解决了自古以来的一个难题,就是以生之有涯追知之无涯。
当然,在现实中,我们所做的就是买一大堆书。
说到这个,最好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书店,尤其是只卖新的精装本的那些书店。这其实是最不该去的地方。我们的第一站永远应该是旧书店。选择可能不那么全面,但我们却可能以便宜得多的价钱找到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