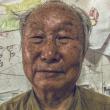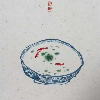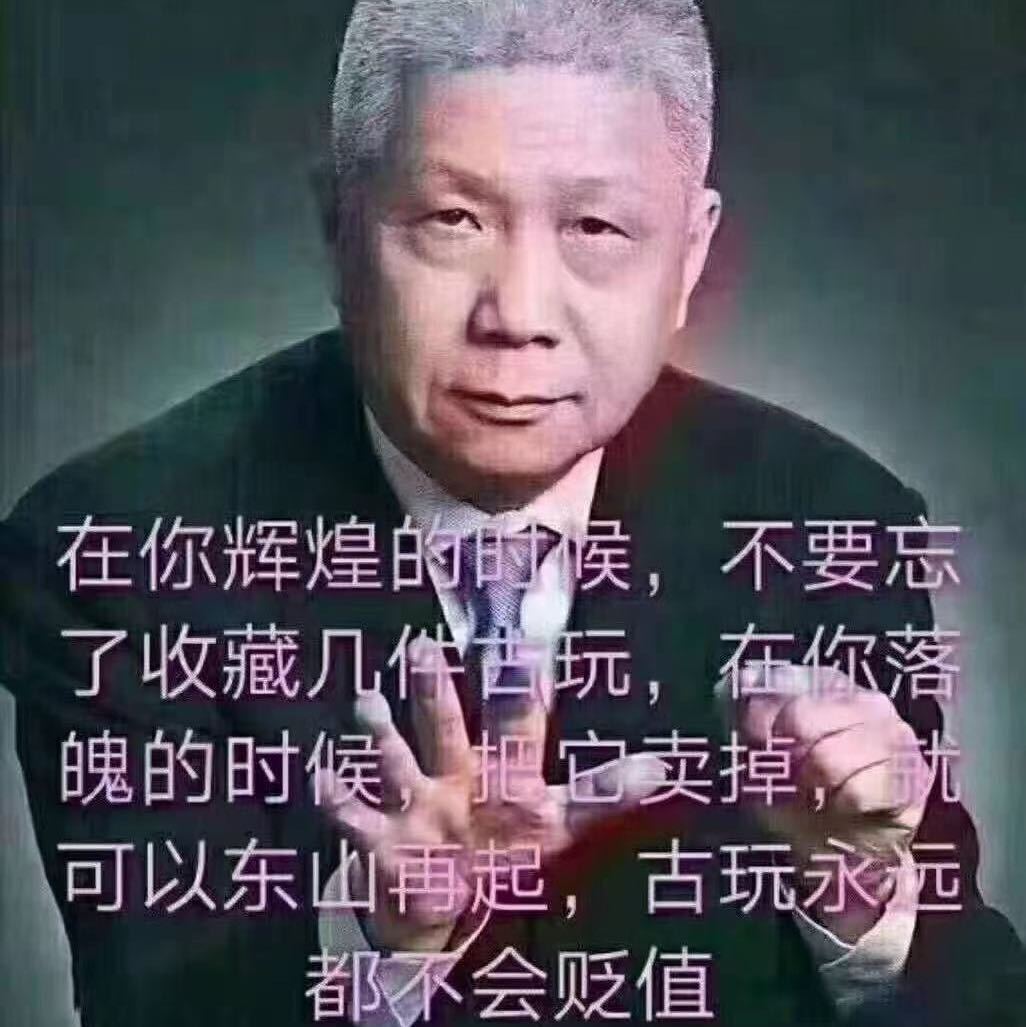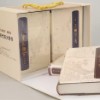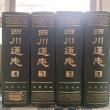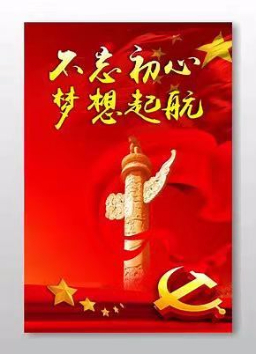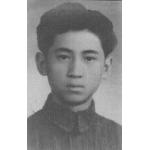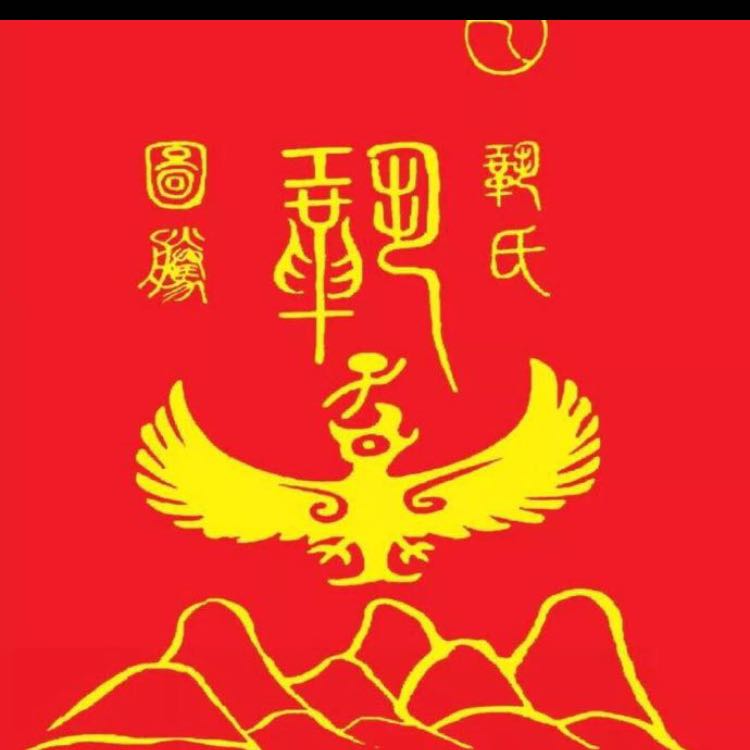我的阅读心灵史
周元川
很多人会说:等有一天我财务自由了,我一定要做我喜欢做的事,例如阅读和写作,研究某种事物。然而,多数人都不会财务自由,所以,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阅读了,回望个人的阅读心灵史,难忘的记忆便涌上心头。
我小小的就喜欢读书,因为家里有许多书籍,都是大哥、二哥读过的小学、中学课本。我常常躲在楼上独自阅读,阅读这些课本成了我的乐趣。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鲁迅、茅盾、巴金、蔡元培、徐志摩,识字的量超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学校墙壁上不时贴出一张落款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的布告,诵读之余,屡屡获得村民的赞赏。鲁迅的“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把文学的描写注进了一个孩子童真的心。一篇题为《爝火》的文章,“看似那般近,又似那般远”,使我沉浸在幻想中。然而对文学爱好的起始,也就是忧患的起始。此后我对文学的爱好虽然没有减弱,但是始终没有正儿八经的跨进文学这道门槛。
我从一所二十余人的村小到几百人的高小学堂,热闹而又新鲜。入学时,参加过地下党的校长对新生进行口试,他问我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姓甚名谁,我一一答对了。无非我平常喜欢看报而已,为了迎合当时学习政治时事的浪潮,校长还把我作为典型,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开学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我把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定义原文照抄,套在我的家庭上,语文老师王涛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都要捉自己头上的虱子,我的作文成为范文,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得最深刻,受到表扬。从心理分析,我这个人恐怕有一种天生的投机本性。同是一个班的学生,缪怀用同学就说了真话,他的父母苦心经营,一家人生活困难,怎么会被划为地主?缪怀用同学受到王涛老师的严厉批评,上报到校长那里,列入问题学生名单,听候处理。对此事我颇后悔,我太左、太激进,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吉人自有天相,缪怀用同学在宁夏当解放军军官的哥哥回来了,学校还邀请他作报告,随后缪怀用同学转学他处,此事方才作罢。
我高小时一位同学叫杨洲,杨洲是位奇才,算术考零分,作文有时考100分,他掌握的词语太丰富,老师也倾倒,只好给他满分。他有一本《成语词典》,我比他小五、六岁,把我当成小兄弟,教我一些新鲜词汇。我知道“一日千里”形容速度之快,他告诉我,“一泻千里”才快呢,拉一泡稀屎就跑了一千里,你说哪个快?当然是“一泻千里”快。我怀着羡慕向他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滥用词汇,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打击美国人,我用“狼狈”一词来代替“狠狠”,结果被老师用红笔透批了一顿,在全班点名批评。老师讲了,狈是传说中一种与狼相似的野兽,前腿短,后腿长,要趴在狼身上才能行动,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我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笑料。这一滥用词汇的事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我对用词造句持谨慎态度,养成了查阅字典、词典的良好习惯,有了纠正别人读错字的本钱。不久,我也弄清楚了,“一泻千里”是形容江河奔流直下,流得又快又远。比喻文笔或乐曲气势奔放,杨洲的解释自然成了一个笑话。
我们村里的杨根长学长,把我视为兄弟,他推荐我阅读《罗通扫北》、《薛刚反唐》,我一点不感兴趣,恶其余胥,我至今也不读这类书籍,什么武侠、神话、演义均受到我的排斥。我的偏激限制了我的知识面,但我终身而不悔。
我初中毕业时,数理化,文史地各门功课均在九十分以上,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三个班第一名。考也白考,1958年的升学考试,连试卷都不批阅。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学收到一张不录取通知书。我想不通拟投江自杀,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中央教育部长陈述我的要求,只要让我继续读书,干什么都行。在等待部长回信的日子里,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别人看了不要了,半价书;一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这两本书赋予了诸多命题以历史的纵深感,是一次直击心灵的体验,使我走出了自杀的阴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的一生,就是奋斗。与其自杀,不如奋斗被杀,我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奠定了我奋斗一生的基础。现在回头看,似乎荒唐得无以复加。但是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思想形成的多元性,一旦你接受了,你就会舍死忘生去奋斗,特别是缺少参照系数的时候。在我个人阅读心态上要首先感谢这两本书。
在第一天的农业劳动中,在冰冷刺骨的荷塘里种莲藕而引发灵感,信手写了一篇报道投到《大理日报》去。当时投稿不贴邮票,对我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投稿正好是一条路子。扛着锄头来到县文化馆门口,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盛产莲根的宾川县……”,引起了我的注意,再往下看,那不是我给《大理日报》投去的稿件内容吗?怎么会在这里。去查了一下《大理日报》,证实了就是我写的那篇稿子,接着收到六角钱的稿费。
这篇报道的发表,燃起了我写作的热情。接着再写了几篇,也被采用了,甚至给《云南日报》投去的都被采用了。这时,中央教育部的回信说,已转有关部门(记不起是哪个部门了)处理,要我直接与他们联系。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谁会管我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不满足于发表两篇报道,我把小小说一类的东西投了出去,想不到也发表了,第一篇是《父子俩》,描写了张小藻父子原先出工不积极,实行小段包干后,焕发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牛刀小试,我沾沾自喜,不是去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系统地去阅读几本文学名著,而是乱七八糟地写起来,诗歌,散文,小说,不一而足,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望,甚至东抄抄西抄抄,结果并未见诸铅字。有一天,突发奇想,把《父子俩》一文的剪报寄到《人民日报》,落款是“大理日报供稿”,企图一炮打响。结果可想而知,大理日报来信了,信是这样写的:
“周元川同志:你竟然以我报供稿的名义,向人民日报寄去你的《父子俩》一文,请你今后注意改正。”
由于我的荒唐,挨了当头一棒。这一棒使我稍有清醒,我想我的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写点新闻报道的水平。
于是我开始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我选定阅读19世纪小说高峰期的代表作。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故事性强,一环套一环,如悬念、包袱、人物间内在关系等,总能达到“无巧不成书”的纯青地步。究其狄更斯本人也不是出生在富豪之家,而是13岁就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去做童工。童工经历给他提供了宝贵的最初人生体验,使他了解社会底层和人生百态。但如果他一直做苦力工,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狄更斯”。他16岁时,做了法院的速记员。正是书中关于速记的描写点化了我,我报名参加了哈尔滨北方速记函授学校的学习,被评为全国优秀学员,取得了哈尔滨市道里区文教科颁发的毕业证书。掌握了速记本领对我很重要,有人形容灵感像手里的沙子,不马上抓住就会从手里流掉。速记把稍纵即逝的想法、灵感等迅速变成文字。中国古人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是这个道理;看到好东西不马上记下来就等于白看了。我记录了周边发生的事,所谓“社会百态”。
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受到批判和打击戛然而止,几十本手稿和毕业证书也付之一炬。历史总有它自身的逻辑,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在“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的自我戏谑,自我解嘲中,于是转移去啃中医典籍。因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予赘言。
除了读书就是寻师访友,我去找我的语文老师吴永湘,吴老师一见面就笑着说:“周元川,你发表了不少小文章啊!”我一愣,连吴老师也看到了。吴老师是我考入初中后的第一位语文教师,有个别的字他不认识,恰巧我却认识,他对我印象很好。他很赏识我的作文,一篇写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的观感的作文,吴老师把它作为范文宣读。一次邂逅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的张继曾同学,他说遇到我很高兴,在北京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北京怎么能够看到我的文章?原来,中央民族学院订有《大理日报》,远在北国的学子,读家乡的报纸自然是一种乐趣。正是师友的鼓励使我的阅读没有完全中断,算是一件幸事。
为了写作需要有选择的阅读,我想把语文基础知识打深一点。通过报刊搜索有没有哪儿办函授的,正规的找不到,找到一家叫中华函授学校的,办了一个《语文学习讲座》,正合我的脾胃。1962年5月,教育部宣布:中等函授师范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完成,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结束。职教社在上下求“业”的日子里,在所谓两条腿走路方针指引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中华函授学校采取函授与面授结合而以函授为主,自学与辅导结合而以自学为主,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结合而以分散学习为主的方式,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一年时间内集中学习高中的语文课程。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目的是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学习语文。
语文学习讲座自1962年9月创办,1966年6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面授和函授的学员三万余人。编辑《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当时在“讲座”讲课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有叶圣陶、冰心、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源、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冯仲芸、赵朴初、赵树理、张健、张志公、张寿康、陈白尘、吴组缃、纪希晨、周振甫、林焘、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蒋仲仁、楼适夷,高森诸位先生。集数十位教育家、作家、语言学家于一堂,给学员讲课,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的创举。
学习期间我跟共同参加《语文学习讲座》的外省学员建立了联系。至今还记得的一个是山东平度的王某,他会画油画,还寄来了一幅自画像。后来他去了东北,因为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闯关东去了。他的来信常常描述劳动的艰苦,但总比在家乡好,能混饱肚子。我深切感到国内还有多少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另外一个是上海奉贤县的陈某。有一天,当时已经到白羊村上门的杨克军,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本国民党时代出版的讲修养的书,内中收了大作家叶圣陶的一篇文章。那时叶圣陶先生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我想试一试叶圣陶先生对国民党时代的出版物是怎样看待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这本书。开个玩笑而已,想不到叶圣陶先生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回了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元川同志惠鉴:所要图书,不知何处出版,故无以应命,良歉!叶圣陶”。
大师毕竟是大师,字写得好极了。1980年,我在炼洞医院工作,看到报刊上有纪念这位大作家、大教育家的文章,我就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理日报》上,告诉读者,“周元川”这个名字,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归来。因为1961年报纸上还见得到我的名字,以后就消失了。没过几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又播了我写鸡足山的散文《滇西明珠》,广播的威力比报纸大,因为那时城区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禁放,不愿意听也要强迫你听,使我名声大振。
我还读了《中华活叶文选》这套书。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1至5册。父亲是我读这套书的有力支持者,买书的钱都是他给的,他说:“国家不会长此以往的,年轻人中断学习就是中断生命。”他认为这套书适合自学,里面的文章不但要看懂,而且要熟读。可以说,父亲为我设计了一条以书为径的人生路。《中华活叶文选》展历史之长卷,萃精妙之美文,我从那里认识了屈原和楚怀王,认识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与先秦诸子对话,与唐宋八大家交友……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科学家都可与之神交。 千古兴亡多少事,我从悠悠的历史中懂得了自古人生多磨难,“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人给了我智慧,也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自强不息的信念。
几千年文明的浓缩,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五册《中华活叶文选》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字里行间我欣赏到古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潇洒,看到“壮岁旌旗拥万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领略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感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同时也听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春风不染白髭须”之类的叹息。我体验着前人倡导的“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修身养性之道。书中的人生是快乐的,能击败现实的苦难。
1979年,我36岁,正值壮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全国选拔中医药人员,我一举金榜题名,取得了中药师技术职称,参加工作就按大学毕业生分配时的工资待遇。1995年我升高级技术职务,需要考医古文,我又轻松过关。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中华活叶文选》和《语文学习讲座》是我陷入迷茫时的精神食粮,在我人生的转折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9年以后,读书虽无限制,但随着命运的改变,忙自己的专业还忙的不亦乐乎,哪有闲工夫去读文学书籍。退休以后,为了消化人生,才按自己的兴趣重新读起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来。我一遍又一遍读《大卫.科波菲尔》,它是我一生的精神导师。我认为狄更斯的艺术成就最高,他编故事的能力使我倾倒,他对人性的关注吸引了我。狄更斯的作品,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人光明和希望。这种乐观主义、希望之光、人性美丽必定战胜黑暗和邪恶的信念,是他的作品拥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
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雨果,《九三年》是他最後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
托尔斯泰是对男女情感、婚姻家庭有深刻理解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是写婚姻家庭的高手,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把男女之情描写得维妙维肖,对小说中的人物在婚姻中的复杂心理更是刻划得极为深刻,他却处理不好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托尔斯泰的新思想,大部份是“社会主义式的”,但他本人却做不到。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若找不到真我。
我们的一生,在不停地告别,告别今天去迎接明天,告别这里又走向那里。告别亲人,却走向陌生。当生命走到尽头,所有短暂的告别变成永远的诀别。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又在浮现,带着温暖清澈的光芒,引领我们走向终点。
周元川
很多人会说:等有一天我财务自由了,我一定要做我喜欢做的事,例如阅读和写作,研究某种事物。然而,多数人都不会财务自由,所以,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阅读了,回望个人的阅读心灵史,难忘的记忆便涌上心头。
我小小的就喜欢读书,因为家里有许多书籍,都是大哥、二哥读过的小学、中学课本。我常常躲在楼上独自阅读,阅读这些课本成了我的乐趣。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鲁迅、茅盾、巴金、蔡元培、徐志摩,识字的量超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学校墙壁上不时贴出一张落款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的布告,诵读之余,屡屡获得村民的赞赏。鲁迅的“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把文学的描写注进了一个孩子童真的心。一篇题为《爝火》的文章,“看似那般近,又似那般远”,使我沉浸在幻想中。然而对文学爱好的起始,也就是忧患的起始。此后我对文学的爱好虽然没有减弱,但是始终没有正儿八经的跨进文学这道门槛。
我从一所二十余人的村小到几百人的高小学堂,热闹而又新鲜。入学时,参加过地下党的校长对新生进行口试,他问我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姓甚名谁,我一一答对了。无非我平常喜欢看报而已,为了迎合当时学习政治时事的浪潮,校长还把我作为典型,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开学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我把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定义原文照抄,套在我的家庭上,语文老师王涛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都要捉自己头上的虱子,我的作文成为范文,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得最深刻,受到表扬。从心理分析,我这个人恐怕有一种天生的投机本性。同是一个班的学生,缪怀用同学就说了真话,他的父母苦心经营,一家人生活困难,怎么会被划为地主?缪怀用同学受到王涛老师的严厉批评,上报到校长那里,列入问题学生名单,听候处理。对此事我颇后悔,我太左、太激进,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吉人自有天相,缪怀用同学在宁夏当解放军军官的哥哥回来了,学校还邀请他作报告,随后缪怀用同学转学他处,此事方才作罢。
我高小时一位同学叫杨洲,杨洲是位奇才,算术考零分,作文有时考100分,他掌握的词语太丰富,老师也倾倒,只好给他满分。他有一本《成语词典》,我比他小五、六岁,把我当成小兄弟,教我一些新鲜词汇。我知道“一日千里”形容速度之快,他告诉我,“一泻千里”才快呢,拉一泡稀屎就跑了一千里,你说哪个快?当然是“一泻千里”快。我怀着羡慕向他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滥用词汇,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打击美国人,我用“狼狈”一词来代替“狠狠”,结果被老师用红笔透批了一顿,在全班点名批评。老师讲了,狈是传说中一种与狼相似的野兽,前腿短,后腿长,要趴在狼身上才能行动,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我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笑料。这一滥用词汇的事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我对用词造句持谨慎态度,养成了查阅字典、词典的良好习惯,有了纠正别人读错字的本钱。不久,我也弄清楚了,“一泻千里”是形容江河奔流直下,流得又快又远。比喻文笔或乐曲气势奔放,杨洲的解释自然成了一个笑话。
我们村里的杨根长学长,把我视为兄弟,他推荐我阅读《罗通扫北》、《薛刚反唐》,我一点不感兴趣,恶其余胥,我至今也不读这类书籍,什么武侠、神话、演义均受到我的排斥。我的偏激限制了我的知识面,但我终身而不悔。
我初中毕业时,数理化,文史地各门功课均在九十分以上,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三个班第一名。考也白考,1958年的升学考试,连试卷都不批阅。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学收到一张不录取通知书。我想不通拟投江自杀,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中央教育部长陈述我的要求,只要让我继续读书,干什么都行。在等待部长回信的日子里,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别人看了不要了,半价书;一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这两本书赋予了诸多命题以历史的纵深感,是一次直击心灵的体验,使我走出了自杀的阴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的一生,就是奋斗。与其自杀,不如奋斗被杀,我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奠定了我奋斗一生的基础。现在回头看,似乎荒唐得无以复加。但是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思想形成的多元性,一旦你接受了,你就会舍死忘生去奋斗,特别是缺少参照系数的时候。在我个人阅读心态上要首先感谢这两本书。
在第一天的农业劳动中,在冰冷刺骨的荷塘里种莲藕而引发灵感,信手写了一篇报道投到《大理日报》去。当时投稿不贴邮票,对我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投稿正好是一条路子。扛着锄头来到县文化馆门口,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盛产莲根的宾川县……”,引起了我的注意,再往下看,那不是我给《大理日报》投去的稿件内容吗?怎么会在这里。去查了一下《大理日报》,证实了就是我写的那篇稿子,接着收到六角钱的稿费。
这篇报道的发表,燃起了我写作的热情。接着再写了几篇,也被采用了,甚至给《云南日报》投去的都被采用了。这时,中央教育部的回信说,已转有关部门(记不起是哪个部门了)处理,要我直接与他们联系。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谁会管我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不满足于发表两篇报道,我把小小说一类的东西投了出去,想不到也发表了,第一篇是《父子俩》,描写了张小藻父子原先出工不积极,实行小段包干后,焕发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牛刀小试,我沾沾自喜,不是去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系统地去阅读几本文学名著,而是乱七八糟地写起来,诗歌,散文,小说,不一而足,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望,甚至东抄抄西抄抄,结果并未见诸铅字。有一天,突发奇想,把《父子俩》一文的剪报寄到《人民日报》,落款是“大理日报供稿”,企图一炮打响。结果可想而知,大理日报来信了,信是这样写的:
“周元川同志:你竟然以我报供稿的名义,向人民日报寄去你的《父子俩》一文,请你今后注意改正。”
由于我的荒唐,挨了当头一棒。这一棒使我稍有清醒,我想我的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写点新闻报道的水平。
于是我开始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我选定阅读19世纪小说高峰期的代表作。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故事性强,一环套一环,如悬念、包袱、人物间内在关系等,总能达到“无巧不成书”的纯青地步。究其狄更斯本人也不是出生在富豪之家,而是13岁就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去做童工。童工经历给他提供了宝贵的最初人生体验,使他了解社会底层和人生百态。但如果他一直做苦力工,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狄更斯”。他16岁时,做了法院的速记员。正是书中关于速记的描写点化了我,我报名参加了哈尔滨北方速记函授学校的学习,被评为全国优秀学员,取得了哈尔滨市道里区文教科颁发的毕业证书。掌握了速记本领对我很重要,有人形容灵感像手里的沙子,不马上抓住就会从手里流掉。速记把稍纵即逝的想法、灵感等迅速变成文字。中国古人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是这个道理;看到好东西不马上记下来就等于白看了。我记录了周边发生的事,所谓“社会百态”。
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受到批判和打击戛然而止,几十本手稿和毕业证书也付之一炬。历史总有它自身的逻辑,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在“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的自我戏谑,自我解嘲中,于是转移去啃中医典籍。因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予赘言。
除了读书就是寻师访友,我去找我的语文老师吴永湘,吴老师一见面就笑着说:“周元川,你发表了不少小文章啊!”我一愣,连吴老师也看到了。吴老师是我考入初中后的第一位语文教师,有个别的字他不认识,恰巧我却认识,他对我印象很好。他很赏识我的作文,一篇写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的观感的作文,吴老师把它作为范文宣读。一次邂逅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的张继曾同学,他说遇到我很高兴,在北京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北京怎么能够看到我的文章?原来,中央民族学院订有《大理日报》,远在北国的学子,读家乡的报纸自然是一种乐趣。正是师友的鼓励使我的阅读没有完全中断,算是一件幸事。
为了写作需要有选择的阅读,我想把语文基础知识打深一点。通过报刊搜索有没有哪儿办函授的,正规的找不到,找到一家叫中华函授学校的,办了一个《语文学习讲座》,正合我的脾胃。1962年5月,教育部宣布:中等函授师范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完成,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结束。职教社在上下求“业”的日子里,在所谓两条腿走路方针指引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中华函授学校采取函授与面授结合而以函授为主,自学与辅导结合而以自学为主,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结合而以分散学习为主的方式,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一年时间内集中学习高中的语文课程。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目的是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学习语文。
语文学习讲座自1962年9月创办,1966年6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面授和函授的学员三万余人。编辑《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当时在“讲座”讲课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有叶圣陶、冰心、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源、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冯仲芸、赵朴初、赵树理、张健、张志公、张寿康、陈白尘、吴组缃、纪希晨、周振甫、林焘、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蒋仲仁、楼适夷,高森诸位先生。集数十位教育家、作家、语言学家于一堂,给学员讲课,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的创举。
学习期间我跟共同参加《语文学习讲座》的外省学员建立了联系。至今还记得的一个是山东平度的王某,他会画油画,还寄来了一幅自画像。后来他去了东北,因为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闯关东去了。他的来信常常描述劳动的艰苦,但总比在家乡好,能混饱肚子。我深切感到国内还有多少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另外一个是上海奉贤县的陈某。有一天,当时已经到白羊村上门的杨克军,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本国民党时代出版的讲修养的书,内中收了大作家叶圣陶的一篇文章。那时叶圣陶先生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我想试一试叶圣陶先生对国民党时代的出版物是怎样看待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这本书。开个玩笑而已,想不到叶圣陶先生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回了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元川同志惠鉴:所要图书,不知何处出版,故无以应命,良歉!叶圣陶”。
大师毕竟是大师,字写得好极了。1980年,我在炼洞医院工作,看到报刊上有纪念这位大作家、大教育家的文章,我就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理日报》上,告诉读者,“周元川”这个名字,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归来。因为1961年报纸上还见得到我的名字,以后就消失了。没过几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又播了我写鸡足山的散文《滇西明珠》,广播的威力比报纸大,因为那时城区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禁放,不愿意听也要强迫你听,使我名声大振。
我还读了《中华活叶文选》这套书。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1至5册。父亲是我读这套书的有力支持者,买书的钱都是他给的,他说:“国家不会长此以往的,年轻人中断学习就是中断生命。”他认为这套书适合自学,里面的文章不但要看懂,而且要熟读。可以说,父亲为我设计了一条以书为径的人生路。《中华活叶文选》展历史之长卷,萃精妙之美文,我从那里认识了屈原和楚怀王,认识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与先秦诸子对话,与唐宋八大家交友……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科学家都可与之神交。 千古兴亡多少事,我从悠悠的历史中懂得了自古人生多磨难,“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人给了我智慧,也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自强不息的信念。
几千年文明的浓缩,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五册《中华活叶文选》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字里行间我欣赏到古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潇洒,看到“壮岁旌旗拥万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领略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感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同时也听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春风不染白髭须”之类的叹息。我体验着前人倡导的“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修身养性之道。书中的人生是快乐的,能击败现实的苦难。
1979年,我36岁,正值壮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全国选拔中医药人员,我一举金榜题名,取得了中药师技术职称,参加工作就按大学毕业生分配时的工资待遇。1995年我升高级技术职务,需要考医古文,我又轻松过关。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中华活叶文选》和《语文学习讲座》是我陷入迷茫时的精神食粮,在我人生的转折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9年以后,读书虽无限制,但随着命运的改变,忙自己的专业还忙的不亦乐乎,哪有闲工夫去读文学书籍。退休以后,为了消化人生,才按自己的兴趣重新读起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来。我一遍又一遍读《大卫.科波菲尔》,它是我一生的精神导师。我认为狄更斯的艺术成就最高,他编故事的能力使我倾倒,他对人性的关注吸引了我。狄更斯的作品,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人光明和希望。这种乐观主义、希望之光、人性美丽必定战胜黑暗和邪恶的信念,是他的作品拥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
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雨果,《九三年》是他最後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
托尔斯泰是对男女情感、婚姻家庭有深刻理解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是写婚姻家庭的高手,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把男女之情描写得维妙维肖,对小说中的人物在婚姻中的复杂心理更是刻划得极为深刻,他却处理不好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托尔斯泰的新思想,大部份是“社会主义式的”,但他本人却做不到。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若找不到真我。
我们的一生,在不停地告别,告别今天去迎接明天,告别这里又走向那里。告别亲人,却走向陌生。当生命走到尽头,所有短暂的告别变成永远的诀别。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又在浮现,带着温暖清澈的光芒,引领我们走向终点。